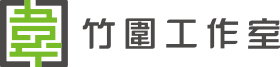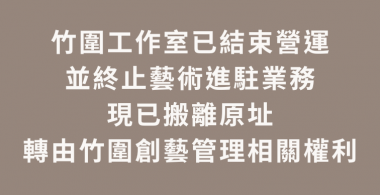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jpg) 竹圍工作室駐村藝術家Irene向新住民姊妹介紹菲國原住民「科地雷拉日」。(陳靖偉攝)
竹圍工作室駐村藝術家Irene向新住民姊妹介紹菲國原住民「科地雷拉日」。(陳靖偉攝)
文/林正尉
來自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紡織教育家 Irene Joy Bawer-Bimuyag 與我,都是同期竹圍工作室駐村的藝文工作者。
駐村時,儘管見面次數極為有限,但在有限時間的對話卻不曾虛耗。好比說,我倆漸漸發現彼此皆對南島文化深感興趣,更甚一步談到臺灣達悟語與他加洛語(Tagalog)用法的重疊性,這些話題種種,都讓我們感到無比振奮。除此之外,當 Irene 知道我的記者職業後自動向我透露:她的外甥在臺中工廠當移工,且將有一場菲國原住民歌舞活動的小道消息。不過因駐村期間,我肩負其他工作,而她亦有節目拍攝行程,相關訊息我們並未積極連絡。
「我們會在同個時間抵達臺中,」我語帶保留,未說盡我倆能否確切見面。
4月24日。豔日灑落在臺中東協廣場四周的異國商圈,沿途的伊斯蘭婦女頭巾、中越文混雜的咖啡招牌及手機店外的玻璃霧面,反射著30度的日光。
一如往常的假日,東南亞移民/工群聚在綠川公園聊天、舉行派對,廣場上湧進參與勞工局主辦的歌唱競賽的各國移工;同一時間,「文化部新住民藝文體驗推廣實驗計畫」與「1095,」合作下,帶著來自臺灣中區的新住民姊妹們進行社區營造見學工作坊;而在附近某高樓的屋頂花園,在臺的菲律賓原住民青年所舉辦的「科地雷拉日」(Cordillera Day),也正歡欣舞動著。
.jpg) 吟唱著宗教詩歌的菲律賓青年男女。(林正尉、陳靖偉攝)
吟唱著宗教詩歌的菲律賓青年男女。(林正尉、陳靖偉攝)
4月24日,一如往常的週末。在「1095,」的江彥杰與官安妮帶領下,我與越南、印尼籍新住民姊妹們逃開附近的官方節慶,緩緩踏上這片「秘密空中花園」。屋頂上的大藍布棚奮力伸開雙翼,向上撐起烈陽,僅容綿綿細光,如塵般的輕撫著眼前數十位菲國青年男女的額頭與肢體,及長青的天臺綠地。
受友人賴奕諭的田野研究啟蒙,我不久前才開始認識「科地雷拉日」。1970年代,在世界銀行、電力公司與馬訶士政權的聯姻合作下,這些強而有力的跨國霸權意圖大舉開發山區,建造水壩,其後果必然引來部落、村莊與祖靈的消失。
為了守護祖先、傳統和山林,北呂宋的原住民族從70年代抗爭至今,早已經歷無以數計的暗殺、陷害與分化。自1984年開始,為紀念已逝的反抗者遺志,加上跨國原住民族抗爭運動的擴大連結,每年四月底都有數千名原住民從世界各地前來參加「科日」的嘉年華慶典,以學習、觀摩菲國原住民的組織動員方式。透過節慶、歌舞、社區培力和跨國聯結,科地雷拉區域人民仍不屈不撓地奮戰,讓北呂宋的戰鬥化身為跨國原住民運動的重要一環。
隻身從樓下走來,一瞧見這群狂歡的菲籍移工們,我心中頃刻升起可能見到 Irene 的預感。果真,「Irene!」我一聲大叫,在圓形舞陣中辨識出她的瘦高身影。
Irene 迅速從舞蹈離開,歡欣至極地握住我的右手。我向她表明我們正在進行「新住民藝文體驗推廣實驗計畫」的社區見學工作坊後,並以北區召集人身分邀請她來為東南亞姊妹導覽「科地雷拉日」。
越南姊妹疑問某些像鳥的動作。Irene 解釋道,他們模仿老鷹或其他飛禽,是為了讓人與大自然結合;同時,也有姊妹好奇何時跳舞?Irene 回答說,部落在豐收或節慶時,都會進行這些舞蹈。
我不確定這些來自印尼或越南的姊妹還想瞭解些什麼。只見她們一個個靠近舞陣旁,近距離拾起手機,但無庸置疑地這場盛宴對她們而言絕對是個意外驚喜。就連身為領隊「1095,」的安妮,也對科地雷拉的發展歷程感到訝異。
不過,我當下想起賴奕諭曾提過,每年為期三天的「科日」常因菲國政府刻意干擾而改期。現今,菲國軍警謹慎於「科日」前後聚集為數眾多的國際媒體和社運人士,不敢「直接進入會場」進行阻撓或鎮壓,因為政府深怕在慶典期間暗殺或迫害相關人士淪為國際大事,但半夜的宵禁仍會造成警民之間的緊張關係。
賴奕諭根據他的田野經驗說,「他們(軍警)會在偏遠村莊或前往節慶的必經道路上實施破壞的工程,包括在路上灑滿釘子、石堆,或製造人工『瀑布』,來干擾各國人士進入。」而這般接近愚蠢的畫面總讓我印象深刻。
但在臺灣,科地雷拉精神似乎長出不同枝枒。至少從基本層面看來,這些活動巧妙繞過官方為移工辦理的「業績型」節慶外,開展出另類的自發性實踐。
無論如何,臺灣「科地雷拉日」不僅凝聚人民原有的環境意識與土地情感,深化原住民部落間團結,更重要的是象徵海外(原住民)移工的大團結。
就菲國「科日」脈絡而言,參與者不僅是原住民身分,是農民,更是需要養活自己、渴望過更好生活的人們。這些意義在菲國移工處境上,不能說不正確。不過,倘若我們從另一種角度認識臺灣「科日」的話,「科地雷拉海外菲律賓工人協會」(Cordillera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Association)能集結北呂宋的原住民青年、菲律賓各省青年、海外移工與在臺灣各縣市的菲國原住民青年,此四種乍看不可能聚集的社群,在一年一度的一日性節慶中相互交織、串起,將大家不可思議的匯集一起禱告、歌舞,也算是一大壯舉了。
.jpg) 科地雷拉日的圓形舞陣。(陳靖偉攝)
科地雷拉日的圓形舞陣。(陳靖偉攝)
.jpg) 竹圍工作室駐村藝術家Irene向新住民姊妹介紹菲國原住民「科地雷拉日」。(陳靖偉攝)
竹圍工作室駐村藝術家Irene向新住民姊妹介紹菲國原住民「科地雷拉日」。(陳靖偉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