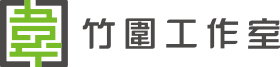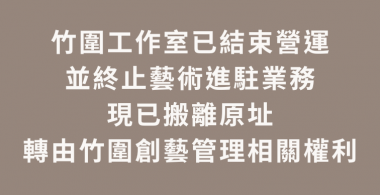據中國大陸「財新網」一項獨家報導(已被刪除),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華南海鮮市場的一名六十五歲男性送貨員開始發燒。三天後,他去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看病。這與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的描述吻合。她說,早在十二月十六日,一名因「未知原因」而發高燒的病人就去了急診科尋求治療。
——蘇曉康,《瘟世間》

在卡謬《鼠疫》第五部中,當新年過後,奧倫城的疫情突然趨緩,整部小說,也就來到了悲喜交集的結局。一方面,市民們終於敢於期待、也已開始談論著「疫病過後要如何重建生活」,彷彿關於未來的想像,即是未來自身的到場。另一方面,疫情無由地來去,卻證實了敘事者李厄醫師的惘惘預感:早自投身防疫起,他就明瞭,我們對苦難的反抗,原本就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失敗」,而這「最終的失敗,雖然終結了戰爭,卻讓和平本身成為無法痊癒的痛」。卡謬藉醫師的陳述,提出一種存有辯證:也許,對集體災厄的見證者而言,在認知到災厄將盡之際,過去仍將重壓他,未來卻尚未抵達他,於是,人們談論的「回歸日常」對他而言,首先意謂著「日常」的突然空洞——人的此在,如今像是未來的幽靈,漫行在未及清理的廢墟之上。
這也許,就是小說最後,當醫師獨自遠望濱海燦亮煙花時,個人心中所感。他感知「失敗」的必然,因歷史總是這般顛錯反覆:死去的孩童藏身在記憶底,形同悲傷的源祖;記憶且倖存的成年人卻更加困惑,一如走入苦難之初的孩童。醫師察知「失敗」的必然性,卻不因此,就縱令自己變得激憤、犬儒或虛無。卡謬以醫師那始終冷靜的敘事,嚮導《鼠疫》這部現代小說,聯繫西方古典文學語境:如史坦納(George Steiner)的扼要詮釋,對西方古典文學而言,其「戒律就是解放」;其「回應和反應的核心,就是強迫的自由」。
正是藉著傾談即將重建的生活,人們對彼此,示現上述「強迫的自由」。這大概也是為何,儘管個人對未來心存悲觀,李厄醫師依舊看重人們各自的觀察與想像。整部《鼠疫》也就由此,將結局收攏為再次的提問:是否可能,無論集體遭遇如何之艱困難解,我們卻不放棄去尋索其中的「可回答性」(answerability,亦是史坦納之詞),以保存一個相對豐厚的人文空間?
小說有其結局,但一部《鼠疫》,要求解讀者越過它,踏勘上述空間,並做出回應。一次駐村計畫亦必有時限,但可能,它透過《鼠疫》文本重新集結、並再次開放的,即是未來的先行:當回顧此在的未竟,藝術家們,同時遠望將臨的創造。於是,當時序來到九月,此次駐村結束後,我們明確可知,印尼藝術家Prabowo Setyadi將持續他的生活共同體共享網絡計畫。計畫終極目標,藝術家構思中的「媒體中心」,雖然未及在本次駐村計畫期限內成立,然而,藝術家已以傳統飲料Wedang Uwuh的生產、製作與上架販售流程,具現共同體經濟條理之一面——物質的順利遞嬗,同時也明喻在疫情僵局中,信息聯繫的初步達成。
亦正是這種經濟條理,顯現比起疫期,更愈常存的日常性:生活不可能免於憂擾、從無傷逝,但逐日逐夜,人們卻以仍能掌握、可以重複的集體技藝,過渡時潮中的暗礁,陳明仍然沉穩的流向。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表面看來尋常無奇的生活行為,反而,給我們帶來莊重的儀式氛圍;像我們,偶遇了並不以戲劇展演為目的的身體行動。
於是,當我們觀看藝術家呈現的影片,請不妨想像:其中曲折道路(多次的出發與抵達),原料採集(從樹上,或地底),家庭作坊裡的人工磨輾、切片、配置與包裝,飲料的沖泡,凡此種種的一次動線紀錄,即是技藝可重複的單元之一。藝術家的意圖,顯然是在落實更多單元,從而,締結生活共同體內,更多向的聯繫。也因此,這裡所謂的「傳統」,既是行動者對昔往的承續,同時,也是對往歷的修復或更新。其中的深意或許是:以當代觀點看來,「傳統」總是種種仍然在場之表意形式的混合物(hybrids)。一方面我們知道,時潮的流演並不可逆;另一方面我們卻也明瞭:只有對時空有另類(非西方線性式)觀念、容許對原初啟示穩定再造的社會,才有望抗拒這種單向的潮流。這需要具體行動,與對「傳統」之不穩定性的宏觀理解。那穿行生活場域的動線,也就勾勒了藝術家對疫後生活的具體想像。
泰國藝術家Preyawit Nilachulaka,則完成了計畫中,五張系列繪畫的第一幅,或第一幅的場面調度(mise-en-scene)靜置圖。因在藝術家構想中,完成的作品應為動畫型態,以此,織進觀看的時間軸:畫作中的火山,會向觀者逼近;死神,也將從畫外移入。於是概念上,目前,我們僅能從時序之定向性的結果,反溯藝術家所想建構的動作文本。倘若直接判讀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藝術家亦以極具個人風格的方式,拼貼各種表意符碼,而以置身其中、主角Bob向觀者的回望(回望的眼神,被遮障在主角眼鏡所反射的光影之後),最終,將懸浮符碼,永久安頓在觀者的視域中。簡單說:畫作總是一種更為理想的觀看方式。
而如果這一理想的觀看方式,即是時序定向的最終結果,我們當然也可以推想,藝術家構思之動作文本的組成邏輯:一方面,是觀者隨主角(與觀察主角的死神),更其靠向死境般的火山;另一方面,是主角將死境與觀者間,逼視出恆定、且終不可逾越的距離。在我們這些觀者與死境之間,藝術家封印了尋求自死者,對不免將行向同一終局之人的回望。彷彿動問死亡,即嚮導餘生。
藝術家循此,將個人辯證視覺化,且立意開展關於「自殺是不是罪行」的討論。奇特的是,當免去神學假設,這個問題將變得相對難以討論,因為在一個世俗化的世界裡,我們首先得自我釐清:「罪」是什麼?就此論述範疇而言,在藝術家構圖中,比例較小、且分身為二的死神,可能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性:我們不免必須追問,祂來自何方,攜來了怎樣的義理或罰則?
死神,開放另一種時序定向性:在系列連作中,彷彿主角的「後生命」,這才要在靠近死境時展開。卡謬亦思索過「自殺」,認為那是唯一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一方面,他描述生而為人,記憶與見證的職責,為我們定義,與其說是神賜,生命毋寧是死亡的給予。卡謬也並不樂觀信任人的記憶力,因為他理解,我們的生命形式,更多是由遺忘所形塑。特別是集體生命形式,當代學理使我們明白:任何想像共同體的歷史基礎,即是對史實的遺忘。
就此而言,日本藝術家Sayaka Akiyama有切身感受,特別,是當十年過去,人們已經極少再憶想福島核災,而東京奧運(原先是以展示日本災後復甦景況為目的之一)最終,又突破疫情限制舉辦之時——可以想像,或許再不多時,人們也不會銘記關於疫病的諸多細節,遑論教訓。遺忘與記憶同場競速,而藝術家駐村期的創作,因為對前者有所體會,於是專注在對後者的留挽。事關在場紀錄的照片、與詩人周予寧通信的文字等材料,成為藝術家創作的素材。而顯然,藝術家此時的創作不為審美效用,只為認知「在場」的確真,以及與他者聯繫的猶有可能。
也因為記憶與遺忘,是這般地不可分割,藝術家預期,在駐村之後,她將持續的生活紀錄計畫,完成之後,不免將是現實與虛擬更複雜的疊合。這意謂著,生活最體察入裡的紀錄者,總也是生活最誠實的背叛者。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將共有困局,反摺為各自獨特的越境。
比三個月的駐村期更長,從二○一九年年底算起,新冠疫情,即將停頓整整兩個地球年。藉前引蘇曉康的紀錄,在這最後之觀察報告的最後,我願再次題記目前就我們可考,疫情最初的星火。既為標注遺忘的啟程,也為擬造記憶的再臨。如三位藝術家的創作,給我們的提醒:在啟程與再臨之間,我們的在場,總是重新的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