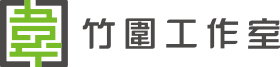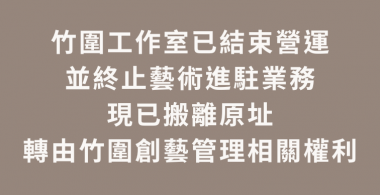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 如果想要發表回應,請先登入。
文/呂佩怡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從2009年啟動,先由命名開始,以行動重新恢復樹梅坑溪之名,開啟人們對於一條溪流的想像。去年此行動獲國藝會視覺策展專案獎助,密切地進行一整年的教育與社區行動方案,探討地方因為不當發展而逐漸失去特色,環境及生活品質逐漸下降時,如何透過藝術學習和行動實踐,轉換思考,重新勾勒一個理想的生活系統/藍圖。五個子計畫包括:「樹梅坑溪早餐會」(社區居民)、「低碳都市村落:流動博物館計畫」(淡江大學建築系)、「在地綠生活:與植物有染」(竹圍國中)、「我校門前有小溪」(竹圍國小)、「社區劇場」(社區居民與竹圍國小自強分校)。此一環境藝術行動不僅是時間軸上的縱向延長,更是地理範圍上的橫向擴大,以及參與者的多樣化,在強調過程甚於結果的特質之下,這個環境藝術行動帶給評論人一個新的挑戰:如何去談一個你未曾全程參與的行動?以何種角度來評價它才不會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此類藝術行動又與其他社會行動有何不同?藝術力量何在?本文將以親身參與的「早餐會」與「樹梅坑溪溯源」經驗為基礎來討論。

與樹梅坑溪建立關係
今年2月中我趕上最後一次的樹梅坑溪早餐會。之前早已知道《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也知道行動所關注的場域離我居住地不遠,我對那邊有條時而出現時而消失的水溝有個朦朧的印象,然而,在我所認識的鄰近地域,環境藝術行動能以藝術之名做些什麼?像我一樣的附近居民們是否認同此行動,他們對於自己的環境願意做些什麼?這些是我對於此環境藝術行動關切之處。
樹梅坑溪是一流經竹圍地區的小溪,源自大屯山系,全長約十公裏,流經小坪頂、竹圍市區,在捷運竹圍站北側注入淡水河。大部分位於竹圍市區的下游河道幾乎看不見的,馬偕醫院門口僅剩「橋」的遺跡,正是樹梅坑溪被埋在馬路之下的證據。在市區時而露出的河道兩側,常可見數十隻排水管,將家庭廢水直接排向溪中。樹梅坑溪中游段為防洪排水,河道被整治為三面光的水泥溝渠,河道裡總可見到不應該出現的垃圾、泡泡、廢電纜、水管等,不時會有異味與惡臭撲面,這不僅因為上游有養豬戶,還有附近的養豬與養鵝戶直接將排泄物排入溪中。溪的兩旁是附近居民的自耕蔬菜區,居民不引旁邊溪水灌溉而是另外想辦法,每一小塊地以自己的方式照料著,生產的蔬菜或自用,或出現於竹圍市場販賣。第一次與最後一次的樹梅坑溪早餐會即在附近的開心園舉辦。

開心園是樹梅坑溪旁的一處花園,是居民劉媽媽實現都市農夫夢的所在。從竹圍捷運站步行10到15分鐘的路程可以抵達開心園,短短路程,地景已從極度擁擠的都市大樓,變成視野寬闊、一整片連到山邊的小農耕種區。最後一次的早餐會以立春時節的白蘿蔔為主要在地食材,劉媽媽與團隊同仁準備整桌佳餚,有蔬菜沙拉、蘿蔔絲餅、蘿蔔絲麵包、蘿蔔湯等,還有劉媽媽熬煮的洛神花茶,不論是熟識的或初識的朋友們喝春酒,拜晚年,聊聊曾參加過的早餐會,以及這一年來關於樹梅坑溪的點點滴滴,還有現場的朋友即興表演起自己作詞作曲的歌曲。這天除了享用美酒佳餚之外,另一個重頭戲是在開心園裡種下原生的樹梅樹。樹梅坑溪之名即是因為早年溪畔長滿原生種的樹梅樹,但當樹梅樹大量被砍伐作為柴燒,樹梅樹的消失也標示著樹梅坑溪在附近居民視野裡消失,失去名字的樹梅坑溪成為一條不知名的排水溝,長期被忽視。此一種植行動標示樹梅坑溪恢復自然生態的未來可能性。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的關係美學
當天我與帶著孩子來參與早餐會的法國策展人Alice Schÿler Mallet談到這個開心園早餐會,我詢問:「你如何看待這樣的活動?如何將之視為一個藝術行動而非普通的鄰裏聚會?」。面對這樣的問題,我自己都沒有把握給予適當回答,Alice不疾不徐地回答:「在法國,我們有『關係美學』論述傳統,大家可以藉此論述去認知與看待此種藝術實踐。」對於不斷開展的當代藝術,此線索提供一個觀看《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之方法。
Alice所談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是1990年代法國藝評與策展人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所提出,他將與觀眾建立關係的作品做為一種特殊藝術類別,以「共同饗宴」,「大家一起來」之氛圍,鼓勵「藝術是為大家的,大家都是藝術家,藝術在日常生活裡」,強調「人」的參與使一般社會行為閃爍出藝術的光輝,例如泰裔藝術家第拉文嘉(Rirkrit Tiravanija)將畫廊轉換成他在紐約的公寓,邀請觀眾來到此地享用免費咖哩飯,以派對為人與人之關係建立的平臺,這是「關係美學」裡著名的案例。
然而,布希歐所提出的「關係美學」僅強調過於樂觀的「關係」而遭受批評。2004年英國藝評與學者畢莎普(Claire Bishop)在《10月》(October)期刊發表一篇文章〈對抗與關係美學〉(Antagonism and Relational Aesthetics),批判「關係」不應只是「關係美學」裡所強調「社區=同在一起」之歸屬感,她認為那些由不安與不適感產生的關係,也必須被視為是一種關係的建構。例如藝術家喜耶拉(Santiago Sierra)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西班牙館的作品,只允許持有西班牙護照者進入參觀,而拒絕其他參觀者,這件作品將人與人之間「關係」問題化。畢莎普的論述拓寬以「關係」之建立做為藝術的一種認知,也讓「關係」、「參與」、「對話」等與社會相結合之藝術實踐(Socially Engaged Art)持續至今。
若以此來看,在《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中,開心園早餐會偏向於前者,正是Alice所謂美好關係建構的「關係美學」,透過聚會形式,每月以竹圍當地所摘種的時令蔬果為食材,如厝角草、綠竹筍、艾草、山藥等,在現場分享在地食物之際,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樹梅坑溪之關係,人與大自然之關係,並交換意見,成為改善在地環境的新契機。然而,其他場次的早餐會,例如「溪水體檢」、「半農半X」等,與「樹梅坑溪溯源」活動,透過實地踏查,讓河川在上中下游所面臨的問題被看見,樹梅坑溪不再是自然的清溪,它成為由水泥構成的溝渠、是家庭及工廠廢水排放之地、隱於柏油馬路之下的臭水溝等。走一趟樹梅坑溪,與中下游被污染的、水泥化的樹梅坑溪相遇,一種人與自然之間不適、不合與不堪之關係,透過境藝術行動被看見與被指認,在此同時,正如「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主策展人吳瑪悧所說:「所有環境問題背後其實是文化問題」,短短十公裏的樹梅坑溪正是台灣以經濟發展為主軸之下人們對待自然的縮影。這種將樹梅坑溪問題化,使議題敏感之作法,正是畢莎普所欲拓展的對抗/對立情緒的關係美學。
我認為若以「關係美學」之角度來檢視,「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之力量在於既掀開與指向環境惡劣之處(惡關係),讓不可見或看不見的問題可見,同時又透過聚會方式在參與者對話之間建立關係(正關係),且讓更多的人都由身體感知的「看見」,產生意識的「理解」,進而鬆動既有結構,產生「變革」之可能。
藝術行動做為改變生活實質的平臺
回到台灣的當代藝術脈絡,我們可從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從吳瑪悧自己的實踐經驗出發,《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可說是回應與轉化她近五年來的思考。2006年吳瑪悧策畫《人在江湖-淡水河溯河行動》,把人帶近河川,透過身體感知重新認識河流以及我們生活的所在。2006與2007年的《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則透過藝術進駐計畫,以「藝術家變居民,居民變藝術家」互為主體性的概念為主軸,讓藝術家進入與住進嘉義縣偏遠社區行動,提出「藝術扮演的不是美化的角色,而是引發、連結、思考的媒介」,這個行動也因為與地方政府合作,創造了介入政策,改善現實的可能。2008年《台北明天還是一個湖》則思考都市發展如何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所帶來挑戰。前者促使吳瑪悧思考「面對巨大的河川問題,如何扎實的回到日常個人生活的實踐,而不是打高空、炮口對著他人?」,後兩者讓她看到「藝術進駐雖帶來活潑的能量,……偏鄉面對的更大問題其實是經濟,藝術如何從作為反思和觀想的媒介,成為可以改變生活實質的工具?」。
回應「如何扎實的回到日常個人生活的實踐?」與「藝術如何成為可以改變生活實質的工具?」此二議題,在我看來《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有三方面的策略:策略一是用人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感受的環境議題為主軸,以吳瑪悧自己居住地附近的樹梅坑溪流域為具體的行動對象,並以日常生活平凡家常的事物做為拉進開端,例如「早餐會」的在地食材分享與在地議題之討論;「流動博物館計畫」的手工修理,反思「一次性消耗」的消費型生活模式;「社區劇場」的生活經驗分享等。透過藝術行動創造對話空間,以鬆動與改變既有結構。 策略二是透過教育系統的直接行動,竹圍國小有三位藝術家進駐,配合課程,帶領小朋友用五官感受周遭環境;竹圍國中則由兩位老師為主力透過水與植物進行在地綠生活的行動。由小朋友連結到他們的家長們,讓樹梅坑溪的議題成為家庭的共同活動。另外,淡江大學建築系同學以建築與都市設計之角度來討論竹圍是否有可能從臥房城市轉變為都市村落、手工城市;附近的台北藝術大學也有同學加入溪流河域調查與居民訪談,或以此流域之問題做為藝術創作發想點。在此策略裡, 「社區」一詞不再是模糊籠統、隨機取樣,或被視為同質之概念,而是更明確的可以用不同年齡層來區分,並採用適合他們的方式來進行,「社區參與」有更實質的意義在此行動之中。
策略之三是結合政策面,將新北市政府拉進來,透過將樹梅坑溪放入官方的「大河願景」計畫之中,以藝術做為想像力的發電器,並以行動做為之後實際河川整治與生態恢復的前導。然而,問題是為何是藝術來做這件事件?《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如何不同於其他社會活動?行動的意義又如何被看待?同樣關注樹梅坑溪,水利局關心的是水量,確保河道排水順暢,不會有淹水之疑慮;環保局注重水質,清除水中垃圾,並對污染者取締與開罰單;都市計畫者思考如何以水域為城市生活支援與休憩空間營造之可能;生態環保專家可以是記錄觀察樹梅坑溪流域之生態,也可以疾呼必須透過恢復自然河道以改善樹梅坑溪生態現狀;社運團體以要求改變為出發點,以激烈話語與明顯調動情緒的抗議方式問題化現狀,以爭取權益。這些人們以科學化與系統化之方式,專注於某一個分工領域,雖然可處理其一面向之問題,但由於缺乏整體思考,以及橫向連結的行動力,而產生許多領域與領域之間的縫隙無法處理。環境藝術行動在此即扮演這樣的角色,藝術做為一開放的平臺,去利益地聯結不同領域者,並激發想像力,讓各自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來對應環境議題。藝術所開拓的自由、自然與開放的氛圍,讓對話成為可能,進而帶來改變的契機,此一特質是《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不同於其他社會活動之處。
最後,我引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來做為我所認為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力量之所在。
我並不是為解決問題而來的
我來到這裡只是為了歌唱
而且還要你跟我一起引吭高歌…… —聶魯達,〈讓那劈木工人醒來吧〉,1948年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先透過居民身體參與的親身感知,讓「人與河川關係」被看見,繼而透過不同個體間的對話與跨領域合作,讓「河川問題」現形,再來基於「環境的背後其實是文化問題」展現「樹梅坑溪正是台灣社會的縮影」,讓「台灣社會文化裡的問題」被看見。《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的到來,是為了讓大家都「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或有看沒有見的,並讓更多的人看見問題,在引吭高歌的同時便是一起合作,動手改變現狀的開端。因此,《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以水連結破碎的土地,以行動建立起與樹梅坑溪的關係,並以藝術之開放性聯結起各專業人員以及在地的人們,嘗試讓環境藝術行動成為改變的力量。
本文出自:呂佩怡,今藝術,第2012年6月期。
讓不可見可見—《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之力量所在(上)
讓不可見可見—《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之力量所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