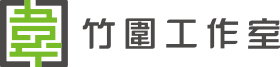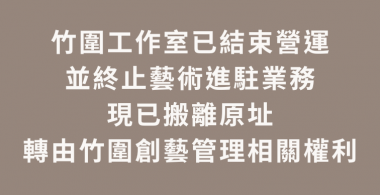文/陳惠文
彷彿是個開端。
接續計劃的策展人吳瑪悧從2006年以《淡水河溯溪行動》的藝術創作表達了河川的議題。2010年開始,她將關心視點放到到流經竹圍的樹梅坑溪。
樹梅坑溪發源自大屯山系,從坪頂里的水尾、吳仔厝一帶流下,續流至竹圍市區並與與來自民生里楓丹白露山區(台北藝術大學後面)的支流交會,再由竹圍捷運北側注入淡水河。吳瑪悧與竹圍工作室團隊發起了〈樹梅坑溪溯溪計畫〉,從淡水河口到山林源頭,一履一步地,跟著溪水逆向流動。她發現,在這短短十公里的小溪,竟然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從鬱蔥林間乾淨清澈的小小溪源,流經人間的豬舍、小工廠、醫院與密集住宅區,原先的淨水變成了惡臭之水,溪野山壁變成了不得不妥協的水泥化與人工加蓋。彷彿是乘載了人間的惡,並默默承受人的欲蓋而不彌彰,它犧牲己身來淨化人類生活,靜靜地流向大海。
於此同時,她與地方居民、多位環境藝術家、跨領域的各界學生,一起研究這條僅十公里的短短小溪,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從地方文史、田野調查、水質檢測,這項對河川的研究舉動引發了台北縣政府水利處的好奇,並引來了日本水利專家,以專家角度提供意見。
為了能夠蒐集到更多關於樹梅坑溪的故事,吳瑪悧開始舉辦了「樹梅坑溪早餐會」,以食為串連工具,從一畝菜甜「開心園」起步,週圍圍繞著好奇的居民、肚子餓的居民,以吸引力法則建立拓展與地方的關係。從探索小樹梅坑溪的過程,藝術家持續思索著河川的處境與解決辦法,由早餐會與居民的茶敘、聊天,又再吸引更多鄰舍的加入,就這樣一圈一圈,雪球越滾越多,可以做的事情越來越多,這一連串的事件,就是畫出《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計劃的前景,獲得2010年國藝會年度的視覺策展補助計畫。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有四個主要的子行動計畫:淡大建築系師生的流動博物館計畫「村落的形狀」、社區劇場行動「食物劇場」、與竹圍國中合作的「在地綠生活」、在竹圍國小的藝術課程「我校門前有條溪」、舞蹈生態系的「水之舞」,以及各種大大小小關於河川的科學檢測與田野調查。還有一個每的月底持續進行的、沒有終極目的隨吃隨聊「樹梅坑溪早餐會」,以食為名的聚會,實際上是人才的串連活動,藝術家仿如老莊進行河川的無為而治,雖然對環保的議題行動是很緩慢與無未來預定的,它正由參與的人們畫出新的關係與發酵關係。
視覺河川――台灣生活景象的共感召喚
台灣的形狀狹窄,山高海拔變化幅度大,雨稠之水便匯集成各地大大小小之川,以及農業的發展讓台灣平地處處可見灌溉渠道,也就是,水的存在路徑與每個人的生存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人對水的現象知覺是深深地印刻於意識中。人對環境的認知,也進而影響人的價值系統建立;河川的存在對人而言,是一種持續性的視覺性,也就是說,人經由感覺器官所了解的河川,是能夠辨識出政府如何治理它、人們的狀態為何,其背後即表現了一種意識型態、統治邏輯。
這代表著什麼?如同吳瑪悧在《人在江湖—淡水河溯溪行動》的創作自述以「環境問題的背後其實是文化問題」為論述子題,河川就是一個城市∕文化的隱喻,從巴黎的塞納河、京都的鴨川、印度的恆河……,人如何對待河川、整治一條河流,並且是一條十公里長的小樹梅坑溪,它的處境與狀態也隱喻了一個竹圍社區、台北都市、甚至是台灣的社會狀態縮影。都市化程度相當高的台灣,人稠密的居住、與產業發展在這過程中讓河水的生態產生變化衰敗,直到當人重新警覺到河川與人類未來生存的關係……。
以河川為題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藝術家們以感性的角度,喚起每個人與河川相處的經驗。從討論河川該如何存在,召喚起對環保的意識、反省人該如何是的生存狀態,這也是《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所隱含的意義之一。
實踐更真實的公共性
比起吳瑪悧先前的《淡水河溯溪計畫》,所拓樸的地理範圍縮小了,但就人的連結意義與實踐產生的力道來說,卻是更實際、更深刻的,不再如此飄忽於藝術家的想像。
在這場串連社區居民、地方團體、學校、藝術家的合作型環境藝術行動,以樹梅坑溪作為一個象徵投射居民的生活狀態。樹梅坑溪以「水」與「環境」的公共議題為先,以「未來居住」的公共利益為皈依,而讓這場藝術與社區產生關係的滑入角色,即是「樹梅坑溪早餐會」。早餐會中居民的參與和互動讓社區的彼此開始凝聚,藝術家透過這種人群凝聚的關係力量來帶動公共性議題的操作,這個環境行動的藝術創作的有效性就在於此。
與其說藝術進入社區,筆者認為是更進一步發展為藝術從社區生長出來的狀態。在環境藝術行動計畫中,藝術家們使用的方式都是緩慢且相當實際的,從與學校課程的紮根,用「食」作為與地方團體的情誼交流、並且連結互相陌生的人(不管是居民或者藝術家),「引誘」出居民的主動性,累積能量地伺機而動。我們可以說,它緩慢的,實際地,以藝術之名在鋪藝術的梗。
並且《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的在地性優勢在於,藝術範圍與竹圍工作室藝術家們的地緣範圍重疊,這種「回家式的」、不流動的藝術家型態,彷彿是「永久駐村」的深耕,使地方與藝術家的主客關係消除,同時也解決了在新類型公共藝術中令人困惑的疑問,也就是藝術家離開之後的倫理問題。
藝術可以是什麼?
整個行動計畫中,藝術家是長時間踐履式的投入,從認識地方的文化推演,時空甚至跨及過去在地的歷史累積、空間橫移人所移動的方向等等,到與地方社群的對話、互相影響……,其藝術性可以說是發生在整個過程中。「當藝術家們偏向以過程作為創作基礎而開放其作品時,意義乃是存在於過程之中,而過程本身並不從屬於任何外在的決定性,因此能夠產生不以物件為基礎的藝術。」[1] ,不單是由眾人所合作的實體物件(即使有共同生產出的物件作品,比起直接將物件認為是藝術,毋寧說那是一種達成關係的手段),也不是只從結案的文件展演就可以感受到的精神性滿足。這種Nicolas Bourriaud的關係美學,「藝術作品的作用不再是形塑想像與烏托邦式的現實,而是在現有的真實中實際成為生活路徑與行動模式。」[2],而這種「臉的面對」、活生生的相遇與碰撞,高度都市化中人的疏離感以藝術之名縫合,藝術從「為藝術而藝術」到對「人的存在狀態」的根本省思,《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所提出的藝術問題,是重新思考藝術家的定義、藝術的可能性,或者是藝術定義的擴展。或者我們可以說,它是以藝術之名達成的藝術家心目中真正的藝術,從行動輻射出文化內涵,樹梅坑溪對城市、國家的隱喻更拉出行動的深度。且它不只是行動的深度,它是一種詩意的文化行動,而且超越政治,它不只是運動,也是藝術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