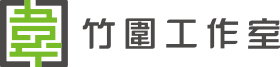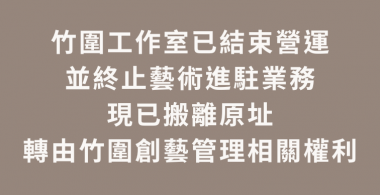文/吳牧青
圖/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文章來源:典藏今藝術2013年10月號no.253
伴隨著具有多元面貌的台灣藝術創作走過11年的歷史,台新藝術獎嚴謹的評選機制,樹立了一定的專業公信力,今年在邁入第12屆之際,為了與時俱進、即時回應藝文生態的發展趨勢,以容納藝術創造更多跨界溝通的未來可能性,決定進行歷年來最大的獎項變革,除了取消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的分類、強化「藝術社會參與性」的關注角度,也設立了ARTalks專屬網站,開放給提名觀察人、藝術家與社會大眾進行最為直接的交流互動。
同樣的,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典藏.今藝術》雜誌的合作企畫,也從過往邀請觀察委員單方向進行各自關注主題的探討,轉為由編輯部自ARTalks的討論中挖掘出能引動思辨的議題,而後邀請來自不同背景與領域的寫作者參與,期待能因此突破既有的限制與框架,以此評論的介面激發藝術與社會、經濟、歷史與哲學等層面更為寬廣的溝通力量。
────────────────────────────────────────────────────────
今年1月,紐約大學藝評學者畢莎普(Claire Bishop)造訪台北藝術大學的一場專題講座「參與性藝術—合作及其不滿」(Participatory Art: Collabo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隨即,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陳泰松於「ARTalks」網站針對這場講座速寫了一篇短評,可以說是為近年台灣當代藝壇思潮與社會環境風向、也為台新藝術獎在第12年大幅度修改評選機制,所寫作的一個楔子。
該篇文中述及︰「『社運者與作者的兩難』是以它們處於同等地位來掌握的,若不是,那便會發生『借用式的資本換喻』──資本在此當然是指文化資本,或以文化資本為主導的政治資本。關於這種換喻,其實也是一種換域(更勝於跨域),一是以作者之名進行社運,是無關於作者的實踐,是作者將它的文化資本挹注社運能量(如學界藝文知名人士),另是以社運模式進行作者的實踐。」如此的速寫,除了做為對於畢莎普於講座所提出「社會參與式藝術的討論,幾乎都集中在創作過程與意圖,或藝術之目的對社會的改善作用,但卻忽視對作品的審美評判」的回應,某種程度也平行對話了當前已全然滲入主流文化風氣的現況,前者反映了名宿的輿論加持作用,諸如名導演、名樂團、名評論人加諸於運動的曝光力量;後者則反映了新型態創作場域的生態結構,諸如文化反堵、以作品為骨幹的抗拒或揭露行動。尤有甚者,誠如陳泰松該文之末段所提「歧異路徑是寓居於反抗體制的陣營,但又異於後者的二元對偶式的批判:它是基進性的奇數之路」,則介於這種「換喻」的角色之間,以近日五月天樂團大篇幅地夾帶社會抗議之聲所形成的《入陣曲》MV文本,則可謂進入這種歧異路徑的討論,在文化評論譜系是否有機會擺脫二元對偶批判的奇數之路。
做為台新藝術獎舊制視覺藝術末代首獎得主,吳瑪悧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也成為新舊制交界間一個得以重新討論並看待的文本。(註1)首先,關於「藝術家身分的宣稱」做為社會參與和實踐之名,吳瑪悧並不以此做為主動涉入的角色,甚至在此計畫的進行初期便以策展人的身分提案,即便是以2005–2008年的「嘉義北迴歸線環境藝術行動」以在地田野的工作模式為藍本,主/被動角色互換之後,社會參與的實質並無礙於「藝術家vs.策展人」傳統角色界分上的切換。再者,面對行動主義者對於社會議題作品採取「有效性」的批評聲浪,吳瑪悧的回應亦鏗然明確︰「我想做的就是『如何透過藝術讓那些議題被凸顯出來?』我們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但是我們有辦法讓那問題凸顯。」
「跨域」的思維若是台新藝術獎新制最核心的梗概,那麼突破「視覺/表演」的分類顯然只是在評價機制中的初階前進,它固然打破專業類屬下的狹小視野,卻猶待指陳出更廣義的跨域視野,如同陳泰松所提的「換喻」或「換域」,倘若傳統初階觀念中的「跨域」只像是如同「劇場混種新媒體」這樣的初階回歸(事實上只是重申了劇場藝術原有的跨域性),那麼,「換域」的再突破即可成為跨域的第二步。吳瑪悧使用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而非參與式藝術,即為一種換喻,由藝術家身分到策展人提案,亦為換域。若論資源上的募集,樹梅坑溪社區得以由藝術行動的提案,到水利署的預算挹注,則也是一種資源上的「換域」,甚至可以推演為藝術的「喚喻」。

至於,畢莎普所提出的質疑核心——關於參與式藝術的評論泰半只注重倫理面,但好的企圖不見得就是好的作品),其實,這樣的批判亦非過度膨脹,無獨有偶,筆者曾聽聞去年上海雙年展策展人邱志杰在觀察其特別展項目——「中山公園計畫」的部分作品時,曾有感而發提到「好像有些藝術家會覺得和民眾參與或產生互動,就達到了藝術介入的目的,如果是這樣,那會不會顯得太容易了?」而無論以畢莎普或邱志杰過往的論述脈絡或展作生產軌跡,確實可排除那種傳統作品中心的基本教義的二元討論,這樣的議題無分東/西方文化,提出一種新型態作品意識的可能美學感知應如何再樹立的質疑。誠然如此急切的呼聲,便來自於過多簡便而輕浮的社群架構出的藝術遊戲,在善意企圖即成立的各種作品生產,俯拾皆是,然而,評論機制對這樣的風潮尚有待建構出堪以爬梳的論述系統。
對此,吳瑪悧則提出另一種關於傳統「社會參與/介入」(social engagement)的「換喻」,她捨「參與式藝術」而就「社會實踐」為第一要件,於「參與」的面向則提出以訂婚為喻的「社會承諾」(同為social engagement詞彙定義)來替換態度輕佻的「社會參與」或暗藏霸權觀念的「藝術介入」(註2),自不失為可行的路徑。繼而,吳瑪悧對於藝術行動的美學感知評價,則採取一種「毋須追問『再現』美學」的表態,她認為行動與展示的再現至多是紀錄技法的再生品,亦即展覽或結案予不在場的觀眾或讀者的必要之惡。
在擴延藝術感知認定的路上,今年台新獎的改制有了一個論述上很有利的轉變基礎,在進行(那些過往不被認定的社會行動)所謂「新型態作品的指認」,藝術評論者的觀點被賦予更大的「換喻」可能性,至少,在辯論101大樓公民反核行動網的「核輻人」,或公民1985聯盟在府前的運動集體標誌、五月天的《入陣曲》的藝術評價優劣的同時(或許,還有陳為廷的那隻鞋子),台灣社會實踐的評論史就正開始發生。
------------------------------------------------------------------------------------------------------ 註1 本文以近期與吳瑪悧訪談內容為主要論點取樣,對話全文可參見ARTalks網站之「藝論紛紛」單元。(http://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13101804)
註2 吳牧青,〈謙卑的藝術︰進入他者之地—許淑真與盧建銘的撒烏瓦知部落啟示錄〉,《典藏.今藝術》第213期,2010年6月號,頁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