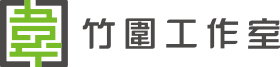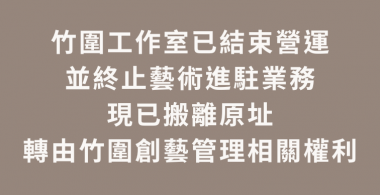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
那個深夜追著殯車淒厲地喊著「媽媽」的人。
那個開著貨車在高速路上流離失所沒有歸處的人。
那個坐著死去被家人抱住頭等待殯葬車的人。
那個隔離在家中被餓死的人。
——微博網友@瑪麗蓮夢六,〈武漢輓歌〉

關於新冠疫情,目前,我個人讀過最刺痛的書寫,是廖亦武的《當武漢病毒來臨》(2020)。如我們已知:卡謬的《鼠疫》,是用沉靜的修辭,型塑經年圍城裡,各色人物的「放逐與離情」。相對於此,廖亦武則以迫切如焚的話語,追記種種抵達真相的困難——關於這場全球性災厄,那核爆般的原點,事實上,仍被遮蔽在層層祕辛中,形同真正的「圍城」。於是,這部作品倒反《鼠疫》拓樸學,收羅了許多不知所終的越界或移動者。其中,有被阻絕在外、必須像偷渡客那樣闖過各式關防,方得返家的武漢人。有各種說出實歷,因此「被失蹤」了的見證者。作品最後,且以上引的〈武漢輓歌〉作結。這首由網友接力創作的長詩,刻印「後事實」時代,人們仍想存真事實的努力:每個封印某人身影的短句,每段信息,都直面不被允許談論的死亡。
這種直面,也重省了《鼠疫》的根本提問:當瘟疫乍然爆發,隨機取走許多人命,這般死難,究竟有何道理可言?在《鼠疫》裡,這個難題,由潘尼祿神父兩度嘗試解答。第一次登壇講道時,他以「激烈強硬的語調」指責圍城眾生,認為大家「罪有應得」,而瘟疫正是「上帝之鞭」,鞭策傲慢與盲目之人自省,於是,「這場傷害你們的災禍其實也正教育了你們,為你們指出了明路」。
神父訴求的,可謂道德論:天罰絕非無由,必然,是因集體生活,早就有悖信仰義理,因此,天罰這才姍姍到來。神父的說法,令李厄醫師不敢置信,因若摘除一神信仰系統,道德論,自有其更歷久彌新的履歷,總伴隨每回集體災厄而返——如我們可能都記得,新冠疫情最初,亦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定調為「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說不定,摘去信仰的道德論,會是更糟的那種道德論:起碼,神父猶力圖以基督徒信念,號召眾生同難;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卻只是冷然地,指出確有一種形同病毒的「武漢人」,該當承受全體「非武漢人」的譴責。
第二次登壇講道時,在對死難實況(特別是孩童之死)有了近身體察後,神父修正他那自覺「缺乏仁慈」的說法,建議大家,「不應該試圖去解釋瘟疫的現象,而是應該盡量從中學習」;只因「最嚴酷的考驗對基督徒而言仍然是特權」;只因在疫病的極端考驗下,關於信仰,「你若不能相信就要完全否定,而你們之中有誰敢完全否定呢?」
神父這回扣問的,是信仰的超驗論:他企圖凝望基於人的視角,必然無法理解,而只能純粹愛重的神格。神父使我想起更多劫餘倖存的信眾。如長崎原爆後,重回浦上河谷定居的被爆者,永井隆醫師。1945年秋,浦上天主堂為八千多位在原爆中罹難的天主教徒,舉辦追思彌撒,永井醫師即發言,表示「他堅信那顆炸彈落在長崎,全是上帝的旨意,讓全日本最大的天主教徒聚集處可以犧牲自己,結束戰爭」。以人的視角,我們或許都能理解的,僅是信仰苦路上,這般艱難之愛的必然武斷。因事實上,長崎原爆罹難者,多數並非天主教徒。
於是,一方面如永井醫師的「堅信」,也如潘尼祿神父的提問,他們的思維,極可能均是不同版本的,對著名「帕斯卡賭注」的重詮:十七世紀,這位數學暨哲學家奉勸我們,在無法驗證的情況下,有理性之人,還是相信上帝存在為好,因為「贏的話全贏,輸的話什麼都沒輸」。他們可能贏得的,不只是「無限快樂的天堂生活」,也是在意外橫生的此世,對種種使人無法平寧之偶然性的有力否決。如此,人仍在苦路上,卻得以從此幸福。
另一方面,如永井醫師的自述,也如廖亦武追記的諸多紀實細節,仍然多憂的此世使我們明瞭:污名與加冕,原來是社會效用相似的一組雙胞胎——有可能,兩者同樣促使我們,不再深思苦難的確切因由。當戰後日本國民污名化被爆者,永井醫師想像犧牲者的高貴;當病毒研究員想像一種「不文明」的「武漢人」,網民們如斯文明地,在網路上點起虛擬蠟燭,哀悼吹哨者之死,彷彿褫奪他生命的,僅是一場使人格外惋惜的天災。
加冕或污名,道德與信念,以及更多更多的集體假設。當思及這些,再一次,卡謬所謂的「正直」,顯得如此必要。「正直」要求我們,祛除種種對集體災厄之確切性的遮障,平視(這非常不容易)、並據實知解我們的生活。這亦是當時序進入八月,當藝術家們完成「疫情下的生活」這一共同子題時,他們各別發現的俗常,將各自獨特而重要的原因。
一種每天重複、「如受困於動物園」般的生活,正包圍泰國藝術家Preyawit Nilachulaka:因疫情形同生活常態,報導好似「無限跳針」。他持續格思「死亡」,於是「死神Furikko」這個角色,終於對他現出生動的形象。做為永遠不死的殭屍,主角Bob的同伴,Furikko彷彿是另一種意義的青春永駐:她身材姣好,手持收割生靈的標準配備——一把大鐮刀。
藝術家或仍思索著以漫畫形式,表現嚴肅命題的困難,但其實,如Furikko的人物造型,所運用的經典視覺印象,已具現當面對嚴肅議題時,漫畫形式可能有的不馴潛能。因稍做研究,我們即知:事實上,在西方,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畫作才被允許表現關於死亡的俗常細節;亦是在那時,那把比例突兀,使人無法忽視並深自恐懼的鋒利鐮刀,才成為死神的標準配備。死神的刀刃內向,彷彿最易殺傷的,僅是追捕著生靈的死神自己。彷彿獵人與獵物同質。這個經典形象,具有一種隱密的人性:死神之所以被造出獨特面目,原就是為了抗議吞滅人之獨特性的大瘟疫,與中世紀以降的宗教權威。於是,Furikko將如何與Bob一同遊歷那個不馴世界?其中的可能性,令我充滿期待。
對日本藝術家Sayaka Akiyama而言,2021年暑熱之季,則同時既是持續的疫情緊張狀態,亦是東京奧運這一全球盛典的舉辦時節。兩者間的結構性矛盾,引起她注意。一方面,在與詩人周予寧線上討論期間,藝術家彷彿拆解編織品一般,藉不同語言的往還,絲縷判讀《鼠疫》文本(text)的質地(texture)。其中的語境誤差與縫合,還原《鼠疫》文本為更真確的素材,而如昔往創作準備,觸發了藝術家個人身心感知的轉換。
另一方面,當東京以奧運盛典,再現自己為全球之城時,藝術家也展開個人行腳,探看可能陌異,或仍可辨識的熟稔。某種意義,這亦是在嘗試判讀語境的往返:就視覺藝術而言,東京奧運,事關在他者眼中,主辦方想怎樣被理想地認知,因此,將如何以特定象徵、符碼或元素,來濃縮再現自我。有趣的是,在這次實地考察中,卻是一個無意中發現的鏡中疊影,最使藝術家印象深刻:附近大樓的玻璃帷幕,將奧運場館變映成特別樣態。無論《鼠疫》或奧運,藝術家都正以貼近的親為,潛入這些普世文本,可能獨對她開放的世界。
使人遺憾的是,在暑熱之季,印尼藝術家Prabowo Setyadi遭逢至親離世,也親歷在疫情期間,無法舉辦俗常喪儀的悲傷。疫情持續緊張,也使他預定的創作進度有所擱延,不過,他預計販售的飲料Wedang Uwuh,已經完成包裝設計,與原料生產規劃。從藝術家設想的創作計畫(個人生活現場,即田調與創作現場)看來,織入現場變數,或實踐時所觸及的局限,極可能,亦是這般創作所欲探究的重要面向。這個鮮活的現場,個人所在,也許,本就需求極端艱難的涉事。
也於是,當藝術家同時,也已在設想種種「之後」的應為,並反向關注「當地因疫情而恢復的傳統習慣」時,做為觀察員,我想致上最誠摯的祝福。這祝福,同時也給遭逢疫情的所有人,包括打完疫苗後、全身酸痛的我自己。實情也許正是:藉著談論彼此的日常,我們卸下諸神暴力而單向的訓導,從而,可能謙柔地,啟蒙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