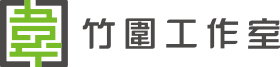文 / 馮忠恬
編輯/張慧慧
當藝術終於自美術館白盒子出走,各種實驗性批判的藝術品進入日常空間,多嘗試與環境產生交流,廣納在地住民的參與,使之成為一種雙向的溝通與理解,從而萌生更多的可能性。台灣的「粉樂町」、「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與日本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皆讓藝術脫離必須在殿堂膜拜的崇高面貌,透過特定場域藝術的具體實踐,凝聚在地共識,使藝術更能發揮所具備的社會改革能量。
「我家門前有小溪,後面有山坡。」是許多上一輩台灣人生活的集體記憶。隨著都市發展、土地變遷。溪流的上方蓋起水泥、築起高樓,破碎成石縫中的渠道、村落中的排水溝。完整溪流,有了另一種面貌。
「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讓藝術進入社區。透過藝術家的帶領,從流動博物館、社區劇場、早餐會等多元的藝術形式,追溯溪流源頭、探討人土關係、尋求美好生活的各種可能。
將視野轉到另一場景。甫於九月底才結束的「粉樂町台北當代藝術展」,自 2001 年舉辦第一屆, 2007 年宣示常態性的舉辦後,將藝術引入店鋪、廢墟等生活空間的模式,開啟了台北東區無牆美術館的新時代。街頭轉角、玻璃帷幕、巷弄裡的咖啡廳,都可撞見藝術驚喜。
不論是「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或「粉樂町台北當代藝術展」,藝術在此都不是一個仰之彌高的論述或形體,而是一個極具生活感與身體涉入的相遇經驗。她們讓藝術跳開了美術館的精緻空間,也脫離了藝術僅銘刻在物件本身的現實主義概念。藝術的價值不僅在作品自身,也在與空間、環境、觀者互動所營造的「情境」裡。
當代藝術走出白盒子
這種和環境、空間充分結合的「特定場域藝術 (site-specific art)」,源自 1960 年代末期的低限主義 (Minimalism) 。當時的前衛藝術家們否定傳統雕塑對內在性的重視,僅將美術館視為乾淨、純粹但毫無主張的展示空間。他們亟欲尋求藝術的擴張性與感染力,探求更具生活化、歷史質地的非正規展覽舞台,並企圖和環境對話,將空間從背景躍升為藝術品的一部分,強調作品與場域間的關係,發展出許多專為特定場域量身訂做的藝術品。
台灣特定場域藝術的發展和裝置藝術密切相關。 1980 年代起,北中南美術館陸續開幕,裝置藝術進入美術館的體制空間,以觀念性的創作,思考作品與環境的關係。和歐美藝術家相同,台灣的前衛藝術家當然不滿足於僅在白盒子裡的展示,而欲尋求各種非正規的室內、外替代空間以作為自主藝術表現,施展才華的舞台。隨著 90 年代初期明訂公有建築公共藝術經費比例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發佈、戒嚴後閒置空間的釋出,以及政府與民間對生活美學的支持,各種環境藝術徵件、公共藝術邀約、特定場域展覽如雨後春筍的出現。
當藝術家不只著重在空間本身,而欲尋求更多的有機連結時,場域的「特定性」會引導出對土地、環境、乃至住民的關心。藝術家們開始以和場域密切相關的公眾議題為創作主軸,在作品中開展出對歷史、族群、階級、記憶等豐富的論述,甚至發展出一系列的藝術行動,邀請群眾直接參與,讓藝術不只是視覺上的美學觀看,也成為撩撥、喚起、嘲諷、凸顯甚至解決在地問題的重要觸媒。
藝術觸媒凝聚集體意識
2010 年日本舉辦的第一屆「瀨戶內國際藝術際」,即是以藝術解決離島人口外移等社會問題的一次具體實驗。策展人北川富朗以「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經驗,串連瀨戶內七座離島,以地景藝術、家計畫 (邀請藝術家在閒置的家屋做特定場域創作) 、藝術餐廳、美術館、藝術表演等形式,讓藝術成為島嶼活化的重要機制。且為了和居民及社區產生更多關連,藝術祭籌備期,執委會即在各島舉辦多次說明會,凝聚居民以藝術活化島嶼,引入觀光人潮的共識。後又在藝術家實際執行過程裡,和居民互動。例如,台灣藝術家王文志的特定場域作品《小豆島之家》,即以在地竹子為媒材,邀集中山、肥土山兩村居民共同完成。居民對藝術進入農村的認同與參與,成為此作品的重要內涵。
進一步地說,當藝術不只貪戀空間特殊性,而具有探求、質問公眾議題的更大企圖時,藝術作為一種媒介,將散落各別之處的民眾凝聚起來,喚起居民對日常生活潛在問題的知覺。因此,不論是「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或「粉樂町台北當代藝術展」,都標誌出美術館藝術形式外,和環境對話的各種可能。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嘗試以藝術凸顯離島特色,邀請居民一同營造觀光之島;「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則希望透過河流身世的探詢,親近人土關係,打破河岸景觀大樓裡,住民白日在市區工作,晚上才回竹圍睡覺的臥房城市型態;「粉樂町台北當代藝術展」更直接回應了城市消費空間裡,殺時間逛街購物與藝術欣賞間的美感關係,創造出藝術生活化的感官經驗,並透過長期性的舉辦,凝聚店家共識,打造出讓城市亮起來的無牆美術館氣勢
隨著特定場域藝術的普遍化,原本的前衛、批判、實驗性格,早已在對場域的深耕裡被「共識凝聚」、「地方打造」所取代。這不單只是把藝術從美術館搬到生活空間的「移動」而已,更是藝術社會、政治意涵的展現。因此,當我們觀看溢出美術館外的特定場域藝術品時,除了形式與象徵之美外,可以延伸思考更多的是:藝術「現場」是否真能作為擾動平靜無波池塘裡的一粒石子,於當地產生一種質變,而非曇花一現的嘉年華式歡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