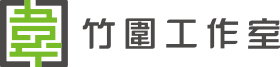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關於「換域/喚喻」的承諾—從吳瑪悧的社會實踐對話藝壇思潮】http://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13101407 刊載於典藏今藝術2013年10月號no.253,是《典藏.今藝術》雜誌編輯部自今年成立ARTalks的眾多討論中挖掘出能引動思辨的議題,由吳牧青訪談吳瑪悧為主要論點取樣的文章。而這場深度訪談,完整刊載於此,吳瑪悧娓娓道來多年來投入藝術社會實踐的動機與理念,計畫與計畫間的轉折也不停拓展著對藝術行動的定義。
---------------------------------------------------------------------------------------------
訪談整理|吳牧青
Q︰請您談談多年下來從事參與性藝術策畫召集的觀察,在圈內的創作者走向這樣的途徑漸漸增加,如今更常出現在一些作品計畫中,就您的理解,藝術家在從事社會參與的重點,若先從您所參與的案例而言,同樣做一個「計畫」,對於不同屬性的觀眾,如藝術圈內的觀眾或是一般大眾,是否會去設定一些區分呢?
A︰是的,我從來不會為一件事情預設了某種結果而去進行考量,當然在這些計畫進行前都會有某些想法或是一定程度的目標,但目標只是協助用來擬定方法,而非一定就會得到預設的結果。簡言之,我所進行的計畫都會有一些很明確的事項或是描述出「我可以為這件事做些什麼」,然後才開始進行,但是進行前會有很長的「實驗過程」,因為我們並無法知道什麼是可能的,於是需要嘗試。每個案子的(實驗)時間也就不盡相同,也無法預設這樣的過程需要進行多久,計畫過程常常便是一邊做一邊看。
Q︰就您認為,做這些計畫需不需進行「藝術家身分的宣稱」這件事?或是進行某種作者概念下的指認?
A︰其實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通常都不會先跟對方說我是「藝術家」。就以「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這個計畫來說,若以竹圍這個地區為中心的社區連結概念來講,和我自己比較有關的是「反淡北快速道路運動」,但這都已經是20年以前的事了,我也因此事和在地而有些連結。不過,也因為我過去從淡江畢業,而淡江建築系如黃瑞茂、曾旭正或後來進入的康旻杰,走出了一條異於建築菁英的路線,當然我們同樣也都算是在文化圈子裡活動,彼此都很清楚在從事的是什麼,加上我住在八里,所以這些對於社區連結、都市發展等等的關心,而淡水八里又自成了一種社區上的連結。這個區域的居民普遍相較於其他地區而言更具有運動意識,而這個地方的運動許多都是在地居民自己參與行動,他們不見得有高學歷或理論背景。從事運動的人是不是就要讀很多知識理論?其實不一定,但是他們都是很有想法的人,因為這個地帶向來有這樣的傳統,所以要做計畫(與社區連結)是相對容易的事了。但通常在淡水一帶的藝術市集或運動都不在竹圍這裡發生,桂竹文史工作室的吳春和就跟我說︰「這裡有竹圍工作室,妳也比較靠近竹圍,那為何在這裡都沒有事情發生?」而過去竹圍工作室曾有一些展覽和河流有關,但與社區之間沒有什麼互動,缺乏互動的主要原因是捷運線的切割所導致的不便,也因為我們常參與竹圍工作室的活動,在一次的聚會上,吳春和就跟我提到「如果要讓竹圍工作室重新找到自己的認同,應該就可以從樹梅坑溪開始。」所以從那個時候我才從這個地方認識這件事情,也恰好當時在北藝大有兼課,就帶著學生做了一連串環境的考察,去了解當地有什麼,畢竟最初我對這條溪是完全不認識的,即使過去曾在北藝大有上課,偶爾進出附近一帶的山路,也不見得有意識去認識這條流域。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做這種跟地方或社群有關聯的計畫,「資源」是很重要的,因為這種事不是我一個人做得了的,而且如果你到了一個地方,他們都沒有環境意識,你還要一個一個去遊說,也實在很困難。所以關於這個計畫,我們平常沒有固定的開會或聚會,但一旦說要做什麼事,他們就都會到。也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網絡資源,所以當我開始在構思這些想法的時候,他們主動參與到「你不用邀請他,他們就會自己出席」。或許我只是搞一個活動,(智囊團)他們就會出現。
這也是我做類似計畫在思考的,我會一直不斷地在前面的醞釀期就不斷地觀察,做一些簡單的擾動,去聊天以理解有什麼樣的資源、有什麼樣的空隙,然後它能不能得到響應?也就是說大家到底關不關心這件事情。在計畫成形之前,那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樹梅坑溪便是經過前面這個很長的鋪陳。
Q︰該如何去評估這個計畫可以從哪個時間點開始?並判斷計畫開始進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A︰例如在計畫進行前沒有任何經費,於是就運用課程上的安排,帶著學生進行田野調查,我用的題目是這樣,因為他們是藝管所的學生,我跟他們說你們搞藝術行政的這些人,那些以地方節慶為名的活動都是一個樣子,就像當時我去嘉義(北迴歸線環境藝術行動)根本不是我自己要去做,它的開始是一個意外,那次嘉義給我的經驗就是,非常多的縣市政府在做文化行政的人,因為不會提案,他們就會去找公關公司提案,申請通過之後,再招標把活動標出去做,通常這種模式便是我們一般人看到的樣子。而嘉義的那次計畫,其實是陰錯陽差,我並沒有抱持想要搞地方節慶的想法,那時候的想法就只是︰當你面對農村,而農村有非常多的課題和挑戰,我想做的就是「如何透過藝術讓那些議題被凸顯出來?」我們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但是我們有辦法讓那問題凸顯,所以藝術通常是在凸顯問題,而不是在解決問題。
所以那次帶著藝管所的學生在做的課程,我試圖要透過這個田野調查的計畫,讓他們意識到「當你做為一個文化行政,你不是去包裝得很漂亮很熱鬧,那些包裝跟地方也不見得有連結,就只是用促銷商品的方式……」並不是說這些事情不可以做,而是它太缺乏視野,那可能還是在末端需要做的事,但在末端之前必須要拉出一個文化視野。「若你不了解地方,你怎麼提出一個想像?」所以我覺得必須要從在地的認識開始,然後去了解那個問題在哪裡,你就有機會去提出一個想法。
因為課程,同學就會做很多練習和訪談,並發現許多有趣的事,而且同學進行訪談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去建立人際關係,很多居民原本你不大認識,也因為他們的訪談和一些社區居民牽上了線。這些都是可以讓計畫順利執行的中間元素。
因此,我沒有辦法預設什麼時候要做(這個計畫),而是看同學們灑出去的網,在田調過程中收回來什麼樣的東西,我也可以在這過程當中去想一些事。於是產生一個作品初步的想法︰「如果這個社區是一個迷宮,那你如何從中找到一些線索?」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那些參與的學生幾乎都不知道「原來學校的後門是長這個樣子,原來四周都是田……」他們通常只是來回捷運站、公車站和大門之間的幾個地方,也才因此知道,原來一些師生就是住在後門附近一帶。這就像是你要從北藝大出發去別的地方,到全國各地、甚至出國,但旁邊的世界都沒看見,這實在太奇怪了。
了解竹圍之後,透過開會討論去理解社區的需要,而當地一直在擴張,變得很擁擠,我們就在想有沒有可能進行一個「生態城市」的提案,重新去思考當我們今天避免不了要生活在一個都市裡面,可是都市的空間一定得如此嗎?沒有停車和走路的空間,孩子沒有遊戲的空間,食物也不知道從哪裡來,大家都吃速食,例如光是竹圍地區就有20多家早餐店,你就能夠想像大家都沒有在家裡吃飯,所以從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就可以了解所有都市的現象,我們就覺得說好像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後來就想到可以用國藝會的策展專案來進行這個計畫,這也是我第一次用這種策展名義去申請,當然真要說策展也許該說「北迴歸線藝術行動」是第一次,但不同的是嘉義是受邀而做的計畫,樹梅坑溪則是主動發起的。
Q︰談到補助機制,因為所有的補助機制都有一個期程上必須完成的時間限制,它給了一定的資源但也限制了計畫的長度,那以此案來說,它必須在兩年之內完成的限制是什麼?妳又如何去克服這種限制?
A︰其實若你再持續觀察這個計畫,會發現其實我們都仍然在繼續進行,所以應該這麼說,我們不是依賴「單一資源」,像水利署因為這個計畫也有資源進來,當然水利署的資源進來不是給我們,但因為這個計畫因此進到樹梅坑溪這個社區,我相信那至少便是好幾百萬的規畫案,規畫完成後,說不定是幾億元的經費進來;所以我們只是啟動一個模式,但是後續的事情不一定要我們做。其實樹梅坑溪這個計畫是從2009年就開始,我們藉由慢慢了解,建立關係,帶著學生去執行。2010年的時候我們就在竹圍工作室做了一個小小的展覽,沒有宣傳,它就像是學生的期末報告,但我們就有個小型的呈現。在2011年開始拿到案子我們就開始進行早餐會,也在耿畫廊做了一次期中的呈現,許多策展案是當年就完成,但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兩年計畫,那個兩年就幾乎稀釋掉了大量的人事費,因為一個案子你拖得越久,人事開銷就變得很多,所以搞不好整個案子的經費有百分之80是用在人事支出上。所以,你可以從我們計畫進行的時間拉得這麼長看得出來,我們是希望把事情做出來而不是只是交出一個展覽。而這個「展覽」就有點像是個移動式的展覽,有點類似我之前在嘉義做的,每個藝術家和社群與社區合作的條件不一樣,有些是和社區居民,有些是和學校,他們活動作息的時間就會很不相同,像學校就是受開學和寒暑假的時間而有限制。呈現的形式也不大一樣,有些是表演,有些是很具體的物件,但我們一方面也是這案子的關係,規定要出畫冊,所以我們最後也是有一個很簡單的成果展示,那多半都是資料性的呈現。雖然在國藝會的策展專案名稱是「樹梅坑溪藝術行動」,期程為兩年,但兩年只是國藝會的行動結束,不代表在這個社區的行動就結束。像是香港活化廳最近也在談和這個計畫合作的可能性,台新獎的100萬獎金也成為了這個計畫後續的基金,所有的人都可以來提案,當然光是那筆基金也不足以運作後續的計畫,我們會再申請一些計畫的經費搭配那筆基金一起運作。
Q:因為這個計畫是兩年的計畫,而台新藝術獎在提名機制上又有「新發表的創作計畫」的限制,那已經進行一年以上的計畫又如何被認定成新發表的創作?
A:這需要去問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才能了解。不過就我自己也曾擔任台新藝術獎的評審團經驗而言,評審團彼此可以經過一個遊說討論的過程來發掘新型的展演計畫,例如我擔任評審的那一年,就提名了許秀雲的「台西壁畫計畫行動」,此計畫也不是展覽的發表,但經過大家討論之後的認可,就可以成為提名的名單;那一年我也提名了樂生,但到後來沒有獲得提名的原因是,每一個提名的單位需要有一個被提名的法人單位,而樂生並無法去指定哪一個單位成為被提名評選的對象代表,包含被提名者的同意,以及被提名者若真的獲獎,那受獎者的認定就會成為一種困擾,當找不到一個對口單位的時候,這樣的名單就無法進入最後的提名表列。
Q:在這類行動方案的作品計畫裡,會不會被認定為「作品」或是「藝術計畫」似乎多半採取事先宣告發表(藝術家)即將進行、或逕行指認計畫開始的作法,那麼,這種有意識的「作品化」行為是不是當代藝術對於「發表形式」的一種難以擺脫的潛規則?這意味著藝術家的「作者論」仍隱性凌駕在計畫項目的本體之上,那除了作者的計畫發表這種指認模式之外,藝術界的各種機制還有沒有其他的動能或可能,去「指認」某些不具「作者權」的計畫作品(甚至從事者自己也不覺得正在進行「藝術計劃」)的存在?
A:我倒覺得這並非「是不是具備藝術家作者身分而論」的問題,不管他是一個人或是一群人做為共同作者,它本來就是有作者的。而你的問題應該是在於提出「它是不是一件藝術作品」,就例如不管是北迴歸線或樹梅坑溪是藝術作品,我也沒有宣稱它就是一個藝術作品,可是它後來就被那樣看待(認可是藝術作品),那樣也很好,但那些行動本來就是一種作品,就作品的概念來看,原本就應該很寬廣的被認定。是不是藝術作品這件事,傳統觀點是要有一種物件去進行視覺上的再現才能稱之為藝術作品,可是這種藝術作品的概念都不斷被打破,從達達開始以降都在挑戰這樣的界線,以致於會有波依斯(Joseph Beuys)這樣的社會雕塑的概念出來,所以這已從原先的有形的(藝術品)到了無形的(觀念藝術)的概念,重點就便不是在於它有沒有物件或是再現的實體,而是說對於作品的理解或詮釋要如何的重新定義,那我覺得這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時候就已經解決掉了,他其實是把所謂的文本和脈絡都視為是作品,所以他談的就是文本而不是談作品。所以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的過程,其實就已經把很多概念給打開了,可是為什麼我們藝術界討論為何常還是老僵在那裡,這其中涉及到的第一個是商業市場,它需要進行買賣,哪怕只是一張紙,觀念藝術也要有一張保證書上面有簽名。同樣的,美術館做為一種展示的機制,它也會窄化我們對於藝術的認知。
所以我一向不會把這樣的認定問題當成是我的問題,那端看你要信仰什麼,如果你是要相信要有物件、要有再現,我也不會因為這樣就說你錯,而是因為那是你的信仰,然後因為我也不是搞理論的,所以我也不會去想到底要怎樣去論述去詮釋。
Q:承如您所說,若那些非物件的、不強求再現的呈現方式為您所相信的,那麼對於那些未參與事件的觀眾,您採取什麼步驟來表現呢?或者換言之,如何在傳統的展示關係之外,另外建立一套美學標準?
A:其實我看過一些辯論,那會回到什麼是「美學感知」的認定上,譬如說我看到一幅畫,而它如何對我「發生作用」?那個部分常被稱為所謂的藝術感知或美學感知,那同樣我們同樣來談這種形式(行動主義),那它同樣也有,例如你問當地的人,很多都不知道有樹梅坑溪這一條溪,但當你帶他們看到下游是條臭水溝,上游沒多遠的地方就是條乾淨的小溪,他們會很震撼,並想說「這是同一件事嗎?」,查覺到這現象的人就會提出很多問題。我要說的是,在這個接觸的片刻,雖然說那條溪不是我畫出來或製造出來的,我只是指給你看,在那個指出過程所引起驚異或震撼,它就是我們在說的「美學感知」,在那個片刻,你讓那些認知之間產生了某些聯想。就像表演藝術,它可能就只有一張圖、一個畫面,那樣的畫面不能代表行動本身,而是一種記錄。
所以說,要如何被再度感知到或是再現這種行動性質,都是一種很大的困難,可是若回到這樣的討論上,是不是就代表我們仍巴著物件不放,去遵循著一種展示價值或買賣價值?也許有些行動式或行為表演的藝術家另有獨到之處,同時可以在行動本身之外另外產生種再現的美學技術,但就如同表演藝術的照片或影像一般,它永遠無法取代表演本身。也有可能你參與了一個行動過程,你不見得有所收獲,也不見得喜歡,但你事後說不定看到了那些照片或影像你就很喜歡也感受到當下感受不到的,但即使是如此,它都不是原本的那件事。
我覺得如果我們一直去追問「再現」這件事,或許不是那麼地有意義,可是我們可以去思考,如何記錄才能接近那件事,當然它也永遠不會是同一件事,所以我們看到做表演的人通常是用影像,那當然都是一種「再現」。
Q: 近幾年有越來越多新生代藝術家也將作品的架構以計畫的形式操作,其中也採取很多參與式的、和社區互動的、走入人群式的開放性作品計畫。然而經過一些觀察之後,會發現其中有不少在這樣的形式之下,其實是另外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行動。例如去年上海雙年展策展人邱志杰和台灣策展人羅秀芝合作了特別項目「中山公園計畫」,邱志杰在觀察其中部份的介入式作品,曾有感而發提到,大意近似這樣︰「好像有些藝術家會覺得和民眾參與或互動,就達到了藝術介入的目的,如果是這樣,那會不會顯得太容易了?」我個人其實對這樣的見解頗為認同,社會參與性藝術有沒有「美學的評價」之必要?如果有,那和一般非參與式作品的評價標準差異,在哪些部分會較為顯著?
A:我不大喜歡「參與式藝術」這樣的名詞,也比較少這樣用,而比較傾向用「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這樣「新類型公共藝術」的出現,其實就是從「公共藝術」跨到一種「新類型」,開始對公眾或公共議題產生連結,過去我們用的一個名詞「social engagement」,每次上我的課我就會要他們討論什麼「engagement」,只有在訂婚是用到這個字,意指一個把戒指套到另一個人的手上,代表著一種承諾。所以那不是我們說,「喔,來玩一個遊戲,然後你們來參與一下……」,用這樣的方式很快能夠理解,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承諾」,而並不是隨隨便便的參與一下;而你提到的「中山公園計畫」,因為我也有被邀請參與,回到social engagement art上來談,它需要一些時間深入的了解;即使你對社區工作再怎麼敏感,仍需花一段時間了解。至於做一個展覽,常常有在地人會幫你把網絡鋪好,讓藝術家進來創作,然後藝術家離開之後在地人仍然可以繼續,這樣才叫engagement。所以這種方式的藝術本來就很難成為一種展覽形式,也很難被展覽。但是也因為展覽的關係,我們被邀請去的時間都是那麼的侷限,到底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我認為端看這個展覽的狀態。例如我這次去廈門,原先是希望可以去一個月,但遇上寒假和過年期間,於是只剩10天左右可以參與,過去對於那個地方是陌生的,即使曾經去過也只是以觀光客的角度瞥過,所以我沒有辦法說我一定可以很快理解當地文化其中的一些意義,我只能告訴策展單位說我試著做看看,但不見得可以做出來。然而展覽通常又是要叫藝術家先把作品計畫寫出來,於是我只能跟他們說「那我給你們我在樹梅坑溪的早餐會,然後再看看類似的概念我可以在當地怎樣發展……」於是我便這樣去了。過去之後發現廈門中山公園有個「相親角」,所以後來我的作品就是關於都市人的婚姻,思考相親角的原因是什麼,那透露著大量從農村到都市的人口,依親的比例甚少,誰也不認識,因此「相親角」就成為一個很有趣的文化現象,另外也發現中國文化中從一夫多妻變成一夫一妻制,就是從孫中山革命之後,將一些封建陋習破除,又產生了另一層對於「中山」的關聯。同時,它顯現了城市人口的文化反應。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非常有趣,總之我認為這個情境可以跟中山公園連結,它也融入了廈門這城市有很多外地移入工作的人口。另外我也發現,無論是男方或女方,他們都會希望對方是有廈門戶籍,原因是中國有各地戶籍管制辦法,如果拿到台灣來看,會變成如果我戶籍在台北,我必須要和有高雄戶籍的結婚才可以入籍高雄,這樣一來,像是已有小孩的家庭,如果要移居求學也成為一種問題。像邱志杰也是,他是泉州人,但他平常都生活在杭州、上海、北京,每次要辦護照就會很麻煩,必須要回去一趟泉州才能辦手續。所以很多現實因素也成為現下對於婚姻選擇對象的條件,這讓我感覺十分有趣。於是就把相親角做成一個行動,中山公園有一個湖,我們就發了一個訊息,「請大家某年某月,我們來遊湖」,湖邊有出租遊湖小船,每艘船可乘四個人,然後這活動就四個人一個單位在湖上來聊「為什麼需要相親角?它到底可以解決什麼問題?」每艘船上我安排了一個主問人,事先和他們溝通好要討論的方向,那個主問人就是帶領這個小組討論的leadership,這其實還蠻有趣的,我們也試著讓成員的分組是(因背景差異)打散的狀態。但最後在剪輯時,因為有些內容涉及隱私,所以有些東西只能象徵性地記錄,讓大家約略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如果沒有參與,也很難知道它真實的狀況。我覺得重點並不在於每一個人在裡面講什麼,而是在於把那些問題透過引發而討論。你看,那樣的情境多好?在湖上,後面就是孫中山銅像,裡面還有個相親角……。所以,我剛剛的重點是說,這樣的行動也需要一些運氣,我剛好花了三天就覺得我可以做這個計畫,所以總共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就回來了,本來預計是先去一個禮拜看看有什麼可以進行的,但去了之後就發現很快就可以做了。這當然是涉及到展覽的問題,像我的作品是一個行動,但「中山公園計畫」最後是要總結移到上海做成展覽,我覺得只是以展覽再現很無趣,所以我到上海的展場又做了一次相親角的行動,在那裡發傳單,參觀的人就覺得很好玩,博物館就變成一個相親角……,我是真的很希望博物館在展期能真正成為一個相親角,但這並不是我的能力所及,因為只是邀請去幾天而已,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當你要求藝術家要做什麼的時候,就涉及到你提供的條件。
作者簡介
吳牧青,獨立策展人、藝文評論工作者。現為視盟後備理事,曾任《典藏.今藝術》採訪編輯、《破週報》記者,演唱會與音樂節策劃主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