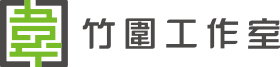贏回聯繫:「Common Plague. Common Decency.」
觀察報告之一. 童偉格
當人們能夠因為專業、醫療或者假期理由而一直連結在上面之前,沒有東西是本土的。本土是分享的可能性的名字,與剝奪的分享結合。它是全球的一個矛盾,我們可以賦予或者不賦予它一致性。每個獨特的世界都為自身所呈現:它是這個世界裡的一個褶皺,而不是獨立其外。
——隱形委員會,《致我們的朋友》
在卡繆的《鼠疫》(1947)中,夏天,正是濱海的奧倫城,疫情最嚴峻的一段時日。彼時,因為死亡人數遽增,加上此城的物資與人力皆都短缺,所以喪儀從簡(後來乾脆省略),只求快速埋妥死者。當墓園的集體葬坑滿載,省府下達公文,徵用原本用來燒垃圾的舊焚化爐,直送屍體前去火化。為了促進運屍效率,奧倫市府遂重啟已經停駛的沿海電車。他們改裝電車,「將座椅拆除、重整車廂與車頭,並將路線轉移到焚化爐附近,使得焚化爐也成為一個起點站」。於是整個夏季,「每到夜深人靜就會看到沿海峭壁邊上,有一列列奇怪的無人電車在大海上方搖搖晃晃地行駛著」。
於是,在那些宵禁之夜,總有人冒險爬上峭壁,等候電車來到眼下,這時,他們就將手中鮮花擲進車廂裡。這是他們仍想親力親為的一種悼念。很奇妙,在讀過《鼠疫》多年以後,關於這部小說,我立即會想起的,不是其中可能封印的種種辯證,也不是類如桑塔格(Susan Sontag)這般精準的評述:以一場瘟疫作為象徵,卡繆呈現了「接二連三的死亡」,如何「賦予了生命嚴肅性」。我印象最深刻的,僅僅,就是這個毫不抽象的細節:花束的拋墜與棲身,伴行向夜,穿過潮聲與靜默,抵達最終的烈焰。
我有時猜想,說不定整部《鼠疫》書寫的,就是這樣一種反語——在小說第一部,寫下「這些散布在歷史當中的一億具屍體,不過就是想像中的一縷煙罷了」,這般冷峻的斷言之後,卡繆卻以更長篇幅,摹寫焚煙中,那些細小塵埃的實存。那無論如何不是幻影。像在為一種必然的遺忘作注,《鼠疫》銘印了記憶者的奮鬥。
這當然也是一部文學作品,對現實世界可能有的注釋意涵:它不在為現世提供簡要的判準,或者預言;它提供繞徑的參照,迫視出一個現實事件的多種可能藏隱的維度。在此,一個細節也可能肇啟某種龐然的觀測。於是,就我理解,本次線上駐村計畫從《鼠疫》出發,用意自然不在對此文本作直接的跨域演繹,而是在以其對現實的參照效用,以文學本然的「繞徑」形構,觸發當下,藝術家們各自有別的創作思考與實踐。
時序進入七月,藝術家們方開始尋找各自的路徑,一切也許仍不可測,卻也格外引人好奇。目前我們確切可知的是,其中,《鼠疫》裡的柯塔與哮喘老人這兩位角色,引起日本藝術家Sayaka Akiyama的重視。我個人認為,這是極有趣的悖論式思維,只因正是這兩位角色,示現了小說裡,其他齊力對抗疫病之正向人物的反面——在一場集體災厄中,兩人別有絕不合群的獨特在場。
哮喘老人,是小說敘事者李厄醫師,在那貧窮城郊所造訪的首位長期病患。比瘟疫來襲更久以前,這位原縫紉用品商就已放棄世途鑽營,進入病榻上的隱居。「哮喘」這病名,像某種存在憑據,使他得以帶病延年,且能全程以一種「老年人的喜悅」,觀察疫病經年且無由的始末。他是小說裡的自我良心犯塔盧,心目中的「聖人」——「如果聖人的特質就是習慣的總和的話」。他也在小說尾聲,以老者的曖曖回望,直解並疼惜塔盧之死。
他的隱密家居之上,那一角從來僻靜的露臺,成為醫師在敘事結束前,最後的立足之地,讓醫師得以獨自追悼逝者,並沉思歡慶。於是,以兩鍋青豆即能精確計時的老人自己,也像是宏觀時間裡,一個本衷如斯的計時刻度——他從來知情疫病的短暫與殘酷。
相對於此,整部小說中,塔盧和醫師唯曾明白指責過之人,柯塔,則以另類執著、絕對微觀的求生意志,一天一天,將集體災厄馴養為個人嘉年華。實情是:當疫病癱瘓了眾人的日常生活條理,也一併擱延了柯塔立即遭到緝捕、入獄的可能性。柯塔因此,在人人受困的封城狀態中,感覺自己,終於和群體有了逼真的聯繫;也因這種聯繫感,而如實察知到一種淋漓在場的自由。
這種基於集體不自由的個人自由,說來頗不道德,但也許,彼時的柯塔,只能專注於自己「對當下的渴求」。根據伯格(John Berger)的定義,並非一切屬人的欲望都指向自由,但自由,總是人對當下的渴求,「被承認、被選擇、被追求的經驗」——自由,是「承認這樣的渴求是至高無上的」。也許因此,柯塔才自我認納,並殷切期盼著當下困局的永不終結。
以同理視角,Sayaka Akiyama思考集體困局中,個體的在場專注或就地疏遠,可能給人(特別是藝術創作者)帶來的被拯救(saved)感,也將循此,反思個人的創作慣性——因為這種私我深知的所謂「拯救」,總也帶起深思者心中,事關群我倫理的個人不安。於是,這說不定將是一次果敢的尋索:在宏觀與微觀的協商中,藝術家正以創作自我突圍。
有別於上述的內向風景,印尼藝術家Prabowo Setyadi明確更關注的,是疫病困局中,在地的現實景況:有關一個生活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及其分享(sharing)網絡。我們可知,《鼠疫》裡,那一列列目的地一致的夜行電車,除了表述一種悼亡外,也極明確地,標注了在警戒時期,公權力對公民,總難免形同極權般的全生命治理。這種治理,連死亡亦監管在內。相對於此,藝術家則企圖複現更為活絡的公眾自治跡軌:那毋須政府規訓,亦能自主運作的,瘟疫時期的常民營生。
藝術家個人生活場域,西爪哇省的賈蒂旺宜(Jatiwangi)由此,成為一個原地流變的田調現場:其中常存的經濟條理,或將在此次創作中,要求近切的深描;其中已遭傷損的此曾在,或也將得到重新的臨摹。某種意義,藝術家是以可見的日常,反窺空氣般無處不在、卻肉眼不可察見的所謂「瘟疫」。於是可能,藝術家最終盼望建立的「媒體中心」,亦有其銘印並傳遞在場記憶的深許——願我們不忘李厄醫師最後的惘惘預感:就在最後一點關於瘟疫的信息死滅之際,瘟疫必將再返。
彷彿反轉上引桑塔格對《鼠疫》的評述,泰國藝術家Preyawit Nilachulaka試圖凝視「賦予了生命嚴肅性」的「死亡」自身,從而接續並更新個人創作——也許個體生命,總不免是此前諸多死亡的收納與新詮。我猜想,一方面,其中基於私我體驗的反思(包括對個人創作慣性的知解,與對個體在場景況的覺察等),或將與Sayaka Akiyama的作品形成繁複對話。另一方面,其中對本土與全球的辯證,也可能在本次駐村計畫中,與Prabowo Setyadi的關注形成多元聯繫。從而,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將必須以目前亦不可測的觀望鏡,才能總體解讀三位藝術家各自的創造。這點,也同樣令做為觀察員的我心生好奇。
上述所謂的「對話」或「聯繫」,其共同基礎是——也許,在當代,瘟疫必然就是一種全球化的事件:空前活絡的跨國性移動,將疫病廣袤織進各處在地的家居,也讓生者由各別家居裡的死難,再思邊防的目的與本質。於是,已有不少人曾推想,若新冠疫情愈演愈烈,會否,這個全球化事件的結果,正是全球化的從此終結。另一方面,亦是在當代脈絡中,我們已知(雖然情感上不一定接受):可能,真的已經「沒有東西是本土的」了,除非,一種以相互理解做為共同訴願的「聯繫」,或「對話」,能一再由我們自主去發動。
我猜想,正是因此,卡繆的《鼠疫》,其中封印的簡明「正直」(戰勝集體災厄的最好方法),與彼此艱難的互解,還是對當下的我們而言,有了嶄新的意義。而做為一名平常人,我當然也慶幸,在這個夏天,台灣不是疫情那般慘重的奧倫城。於是,如本次駐村計畫,一點一點,我們得以在自己立足之地行所應為,贏回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