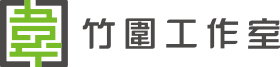六月的觀察記錄。
從三位藝術家在六月對於駐村計畫的分享以及計畫執行的討論中,我發現有三個不太一樣的面對疫情的方式,這些或許與藝術家們個人面對災難的想法,處理疫情的態度以及消化疫情所帶來的苦痛面向差異有關。而藝術家們對疫情的反應,落實於創作中,所結出的果實似乎與卡謬《瘟疫》這本小說中對於災難的態度不謀而合,或許這顯示了大環境的動亂下,即使在不同時期、地區、國家,人類終究還是有某種趨近相同的習性。這是我認為六月會議討論中最有趣的部分。
印尼Jatiwangi的藝術家Prabowo是以食物分享、共享經濟及建立媒體中心作為計畫的初步方向,這是較為主動的行為,主要關注在社群建構,旨在維繫社群內人與人的連結,並且希望透過正確的資訊傳播,使社群內的群眾不因為資訊落差而恐慌,而食材的串連分享也使得社群親密感加深,更可以協助到因為疫情而有所影響的食物供給鍊。
Prabowo還關注到這種社群建構容易成為一次性用完即丟的可能性,思考如何維持農場食材分享的資源配給問題,不過度使用,維持未來存續,長期經營。在這裡,我發現的有兩個主要狀況,首先是「食物」這一點,在「瘟疫」(原諒我沒有更好的形容近兩年的狀況)蔓延的狀況下,這是最主要能夠讓人民安心,撫慰人心的東西。再來是,「資訊傳播」,在瘟疫蔓延人心恐慌的情況下,如何將資訊正確傳播出去,也是維護社群安穩的重要關鍵,Prabowo體認到Jatiwangi社群網路的匱乏,希望能改變這個現狀。而資訊傳播的落差問題,與台灣目前所處的狀況有一些相似,各種新聞雜亂,差別是Jatiwangi的社群網路落差導致資訊無法散播,而台灣則是資訊過量使得每一則消息的可信性都降低。
泰國的藝術家Preyawit計畫以漫畫創作反應Covid-19疫情發生在人心理的變化,他主要探討的主題是死亡,預計創作一篇以Bob為主角的漫畫,漫畫內容概要是主角染疫後死亡卻又復活,如僵屍般半死不活,不斷嘗試各種死法,試圖找到結束這痛苦的方式。就我看來,這個計畫雖然是藉由復生的主角尋找死法的角度著眼,可以說是主角的「尋死」之旅,在故事中,通常驅動故事前進的動力是角色的「想要」與「需求」,「想要」通常是外部的,很明顯的,如Preyawit所提出的漫畫創作計畫,主角Bob很明顯即是「想死」,然而他的「需求」是什麼?我想這才是這個計畫最關鍵的所在。「需求」通常是內部的,主角通常會領悟自己的「想要」究竟是為了什麼,而這個領悟會從內而外改變主角的行為和心境。我認為Preyawit的漫畫創作目前看來是試圖處理人類(或者說,自己)面對疫情時期那被「卡住」的心情,我這裡指的「卡住」,意思是,你知道你在這裡,你想去另一個地方,但你就是他媽的沒辦法過去。而這狀況在疫情中我想是更明顯的,在卡謬的小說中,疫情封鎖是以封城進行,台灣目前還沒有封城過(非常感謝),乍看之下或許封城會是一個很明顯的「卡住」,因為人不能移動外出,然而儘管只是這兩個月的三級警戒,不至於不能外出,但在台灣原本就不愛外出的我,也仍然感覺到某種被什麼限制出的煩躁感,那種走不出來,困在一個透明小泡泡中的煩躁感非常明顯。在Preyawit的計畫中,可以很明顯看出其試圖面對疫情,不再逃避的決心,而這樣的決心也顯示在其漫畫角色Bob的設想中。
日本的藝術家Sayaka Akiyama則是透過限制創作媒介反應受到疫情影響的身體變化。原先她多半是以個人設身處地的經驗來創作,而原先這些經驗多半是有實際殘留物的,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拿過的衛生紙、針線、外帶食物袋等等,各種只要是你生活在這個世界,就必須留下的痕跡,那些「經驗」,在疫情嚴峻的日本受到限制,Sayaka Akiyama無法到處移動留下痕跡,再收集這些痕跡為實體素材做物質創作,因此在這次的創作計畫中,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首先她決定採取數位化的決定,這與疫情迫使大多數活動都轉為線上相關,這也限制了個體的經驗殘留物僅留在數位媒介內。再來則是數位化後所發生的身體空缺,沒有留下任何實體物質能作為經驗殘留物的創作素材,數位化後,僅能將想法透過文字記錄。在Sayaka Akiyama的創作計畫中,可以發現最明顯的是,原先很「此在」的狀態被拔去了,身體所留下的經驗殘留物是很此在的東西,折爛一張紙條所留下的爛紙條,是很觸覺感官的,手指摸過那個紙條,再將紙條撿起,以手指拼貼縫製或者其他,這樣的觸覺感官在疫情後數位化的狀況下被剝奪了,而數位化也容易使得情緒殘留效應比實體化更嚴重,這是因為在感官體驗的當下,人是沒有辦法思考其他事情的,跳舞的人進入了跳舞的情境,就只會跳舞,自己就會成為動詞,然而數位化的人類是不斷地困在過去以及未來的薄獄中,幾乎很難進入「此在」的體驗。因此,Sayaka Akiyama透過這樣的創作限制來反應疫情帶來的結果,主要看起來是旨在呈現身體的「不在此處」。
就我觀察首次交流以及公開會議的結果,由於我沒有直接與三位藝術家談論過主題內容,因此這僅是我個人就手頭現有文本資料所做出的觀察猜想。我認為,藝術家Prabowo傾向希望在疫情下建構社群共同體,使得社群活絡,能夠彼此維持保護,而藝術家Preyawit希望克服對「卡住」的恐懼,面對被困在一個不見天日的疫情烏雲下,自己精神的恐懼以及如何自處。藝術家Sayaka Akiyama則是希望能表達出受到疫情影響而被限制的感官體驗。而在這三種不同方向的駐村計畫中,我卻能看出同樣的堅持,而這堅持和卡謬於《瘟疫》這本小說中,我認為最有趣的一個概念不謀而合,就是災難會降臨,人只要做好自己原本就應該要做的工作本分,就已經是在對命運進行抵抗。三位藝術家都試圖以自己的方式面對疫情所帶來的改變,並且試圖在混亂的日常中保持清醒,不被恐慌帶走。
在《瘟疫》這本小說中,有名原本想要逃離,最後改變想法的記者,他的想法大致上,是從原本認為自己只是局外人,不想參與任何城內的問題,也認為這瘟疫與自己毫無關聯,只想快點找到方法逃出城市。但最後他體認到,他已經親眼見證了這些災難,自己與其他角色一樣,都是這城市的人了,這件事情是所有人的事情,所以我們應該一同面對。我一直都認為這本小說很有趣的地方不在人性被災難誘發出的陰暗面,甚至也不是在光明英雄的那一面,而是在面對災難後,體認到災難就是會出現,我們都很可能不會劫後餘生,但我們還是在這裡,我們還是在做我們原本就要做的事情,因為我們是我們,我是我,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改變這些。
在疫情似乎不會停止的現在(雖然感謝台灣,我們似乎快要撐過來了,至少在我撰寫這篇稿件的此刻七月八號),我時常會想一些平常不會那麼關注的小事情,像是如果死掉之後只是去了另外一個地方而我必須繼續在那裡過完最慘的那一天重複一直重複直到某隻宇宙章魚覺得開心了才把我從宇宙消除掉——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不會其實早就已經死了?我在想面對一個看似沒有未來,也不像是會馬上爆炸的情況,那種悶火慢煮的感覺,是非常凌遲的。而我們似乎也逐漸有了共識,儘管疫苗打了,也仍然可能會染疫,病毒快速變種,或許口罩真的會成為我們未來多年的日常,一開始當然是很痛苦的,沒有人希望災難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會不會真正的解決方法,就只是,承認這件事情?承認災難已經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都不可能倖免於難,臣服在不管是那隻宇宙章魚,還是宇宙透抽的觸手下,接受淋在我們身上的大雨?
接受我們必然的全身濕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