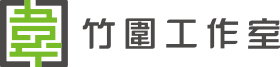在卡謬《瘟疫》這本書中,最先抓住我目光的是書中一個小小的的片段,在小說敘事者開始敘述整個故事的開始不久,李厄醫生走出自己的診所,路邊有個死老鼠,他踢開了這隻老鼠,最後意識到不該把屍體置於原地,通知門房,但門房的態度卻很反抗這個「事實」,對醫生來說這個事實只不過是一個有點怪異但還能接受的狀態,對一個管理樓房的門房來說,卻是一個不能接受的「謊言」——這個對立的結構在故事的鼠疫發展愈漸嚴重之時,會不斷重演在各個角色之間,而一切都似乎呼應回開始的時候,李厄醫生和門房兩個態度的差異,一個平常就已經是面對生死的醫生,和一個管理大樓維護居住品質的人,兩個不同的角色,遇到同一個「災難」的時刻,所產生的不同反應——正如同小說中寫到的「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卡謬小說書寫有個有趣的點,便是很多話語獨立而看,意義和置入語境脈絡中都會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在大多數人不願意承認現實情況,也就是鼠疫蔓延的時刻,這句話是凸顯了人類的無知,也就像是小說中所說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與罪惡無異,帶來同樣損害。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但如果放置於故事開頭的語境中,回歸到那個小小的診所前方,小小的走廊,醫生和門房的應對,這則是凸顯了兩個在這個社會中擁有不同「功能」的角色,所應對這個世界現實的態度。而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例如書中說道,大致上那一段落講述過份誇大美好的行為,或許這樣子會不知不覺鼓勵了人類糟糕的一面,因為人們只關注特別值得關注的事物,冷漠、麻木不仁反而會成為常態。在這樣的思考辯證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故事中有許多內容看起來是在講述某個東西,實則卻是在講另一件事情。而這樣的恍惚,游移狀態,也和我這次觀察藝術家討論的感想有些相關,這裡先讓我預留一個小星星記號,留待後續解釋。
撰寫這篇觀察稿的時間時間到了七月底,發表將於八月,而在七月分享會的過程中,這次藝術家分享計畫內容的發展,時間正是剛好搭到東京奧運以及台灣疫情逐步趨緩,泰國和印尼以及日本的疫情卻似乎又出現膠著狀況,我作為一個觀察者,也在網路尋找各個國家的資訊,試圖去更加理解這些藝術家所面對的現實狀況。泰國藝術家Preyawit(Palm)用類似動物園(聽起來更接近於監獄)的說法來形容自己的新生活,待在原地比起離開更好,但待在原地的痛苦也沒有因此比較減少,這似乎和《瘟疫》小說中所說的那「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不謀而合,這似乎也使Palm的創作更多了比較灰暗的呈現,「死亡」化作一個看起來可愛的舉鐮刀角色,而在Palm的一些圖畫中,也呈現出發生在Bob身上的一些恐怖卻又看起來可愛精巧的東西,如身體突出異型,膚色如美國小兵小模型常有的深綠色模樣,呈現死亡與生命的拉扯。在泰國最近的疫情動亂下,我相信藝術創作會變得更加困難,不如同多數人或許會認為動亂激發靈感,但我確認為在動亂中要靜心思考外部環境以及內心反應是相當困難的,或許在八月時我們都會有機會看到Palm如何在這艱困的環境底下製造出更有趣的故事,以及這些故事如何反應他所處的國家。透過一個介於生與死之間的角色Bob以及新角色死神的故事線,如何反應藝術家在這個生死動亂如此快速,每天關於疫情、關於爭鬥的消息都快速得讓人難以消化的狀況底下,怎麼用藝術反應人生。
日本的藝術家Sayaka,七月則是與顧問詩人周予寧以信件往來的方式討論《瘟疫》(或譯鼠疫,有不同版本的譯本),在其中我認為有趣的部分是信件翻譯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資訊細微落差,或許與印尼藝術家Prabowo媒體中心分享資訊的構想有相互呼應之處,但前者是享受於這種些許的資訊落差,而在這細微落差之間尋找藝術萌生的縫隙,而後者是試圖弭平那落差使得一般無法接受資訊者掉進深淵的可能性。Sayaka由於處於日本,東奧正在舉辦,能以一般人最可能接近會場的方式,去體驗日本奧運所造成的人類體感差異,在Sayaka的分享中,可以很明顯發現,Sayaka困索於日本政府不顧疫情升溫舉辦東京奧運,而這行為受到責難,疫情的疫苗問題、人民的秩序問題,也在媒體渲染下不斷加溫,抗爭氣氛提升,然而東京奧運舉辦之後,卻又似乎凝聚了大部分的民意,使得人民暫時忘記了疫情的困難,為什麼日本人民能同時在抵抗疫情,不願意疫情加溫的同時,卻又這麼熱情參與奧運,觀看比賽,前去館場拍攝照片?
而這些思考也在Sayaka看到人們都在館場前自拍,得到一點解釋,她認為那些人幾乎就像是和小說中所說的一樣,眼睛是睜開的,人卻不在那裡,記得我先前留下的小星星記號嗎?我現在要解釋了——我認為這其實是必然發生,而且必要發生的狀況,不是因為人們需要偶像英雄來崇拜以忘記自己的生活(或許是),這在表面上看去或許如此,人們或許就是對於現實遺忘,掉以輕心了,但更重要的,至少在我看起來,則是人們需要擁抱——或許是一個很陳腔濫調的說法,但人們需要一個什麼,來相信事情沒有那麼糟糕,來迴避自己糟糕的人生,來透過一個去那裡的方式,去躲避掉自己不在這裡的事實——我覺得觀察Sayaka思考日本人民對於東奧,媒體對於東奧奧運的矛盾態度,是很有趣的,因為這些矛盾表現,也都存在於《瘟疫》一書中,而這似乎都與人類與人類彼此之間,需要穩定的連結有關——有時候我們是可以為了那個連結,而去受苦,而去承擔風險,講直接一點,寧願承擔世界末日的風險。
東奧事實上,就台灣難得維持了去年整年的相對疫情穩定,今年在爆發後逐漸趨緩的過程,相對於其他國家封城的嚴峻程度,台灣至今三級警戒也未有太過強制的限制,人民仍然能夠外出,然而這樣的情形在維持了兩個月之後,仍然使得民眾開始怨聲載道,而這時候的東奧出現,對台灣人來說,反而是一個凝聚注意力,分心的途徑。而顧問以及Sayaka在信件往返討論到的,關於柯塔似乎希望疫情發生的心境,也是很有趣的觀察,就我觀察,那與舉辦東奧的概念有些類似,也就是,以一個災難來換取另一個災難,以一個痛苦來更換另一個痛苦』——東奧或許舉辦後會使得疫情更為嚴重,但也可能不會,而無論如何,奧運比賽已經使得原本的疫情災難,被轉為擔心另外一種災難,這樣的轉換,我認為是人類很正常的心理機轉,而那也或許,可以說,就已經是個擁抱。
藝術家Prabowo和自己的家人所住之處印尼重新陷入封城狀態,這影響了他原本的創作計畫,主要是在烹飪藝術駐村以及生產在地商品的計畫。在疫情嚴峻的過程中,Prabowo表示所處社區似乎因為疫情而恢復一些傳統習慣,如在門口放置一盆水讓所需要之人洗手洗臉和解一時之渴。而Prabowo他們也決定,透過自行生產引品,降低成本,使得商品能較好在在地商家販售,而他們預計製作的Wedang Uwuh飲品,而關於這飲品的可能功效以及問題,他也預計撰寫文章發表於自己的網站,依舊是延續了上個月計畫討論中,透過以媒體中心傳播資訊的核心概念。而Prabowo說到無法參與親人的葬禮,這樣的生死闊別,強迫被留在原地的人,去面對這一切苦難,並且意識到,如果自己不離開「現在」,或許唯一剩下的方式,只有接受「現在」即將成為未來——而這如何能讓人不恐慌害怕?
就觀察員的角度,我觀察到不同於六月時候相對平穩的狀況,七月開始,似乎藝術家們都隨著疫情的影響,而有了明顯的心境差異,而這些心情差異,也逐漸反應到他們考慮作品的執行製作方式。但我不免發現我們似乎都成了現實的幽靈,被困在一個動物園中,被困在一個此在與不在的狀況裡頭,此在指的是我們確實存活於此,東奧也如期舉行,大多數城市也開始解封了,我們似乎正逐步在邁向要將Covid-19視作一種可能的常態裡頭了,那是我們的「此在」,但我們同時也不在——我們並不真的走到了能夠面對那個現實的狀況,我們或許都還處於更接近《瘟疫》書中的門房那個角色開始時候的狀態——我們或許都還不能承認,一切就要毀滅,而我們對此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