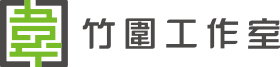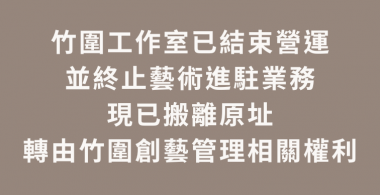採訪、撰稿/ 張姿婷
攝影/ 黃煒鈞
「聽我說!」我興奮地向他展示近期的發現:
「原來在好幾世紀前,就有專門在塑造靈魂的工廠了!」
「那裡面的工人個個面容模糊…」
「…哪有人形容臉長得『模糊』?」他不耐煩地說。
「文獻上是這樣記載的。先別打斷啦,讓我繼續說下去!」
「工人們將一個個美好、完整的靈魂,都丟進鍋裡加熱、融化,再倒入模具裡壓製成型。
一些熔點高的,尚未完整地柔軟,成型時就被模具給壓碎了;一些壓模時有溢出的部分,被精準嚴苛地削去;還有一些非均質的,在成形過程中缺角、坑巴,甚至內裡空洞的都有。
損壞的都將淘汰;不那麼嚴重的,補土、打磨後,也勉強算是個次級品。
最終它們被分級,依照級別漆上顏色。值得一提的是,那時顏色有所謂的『是非之分』,什麼顏色『正確』,就漆哪種。」
-
「這之中似乎哪裡出了問題?」我正思索著。
「…有嗎?我沒什麼感覺。」他不耐煩道:「不說了很累…明天還要上班啊。」
-
「一定有第三條路。不會只有對與錯兩種。」她說:「但那時的我們不會那麼想。」
-

採訪地點位於瑋倫山上的工作室。那天,她開車來接我們跟Maggie。
去往山上的路綿延安穩,似將溺水者打撈上岸的網。綠意是無限延伸的卷軸。
城市不斷後退,緊繃的身軀逐漸鬆開。
靜心創作前,褪下沾染自城市的躁動。
「這是一段儀式性的過程。」她說。
-
流暢精確的敘述前,最先觸碰、連結我的,是瑋倫對萬物的疼惜。
-
做為母親。
做為藝術家。
各個角色的劇本,字裡行間藏有一道道線索。
領她遭遇生命之路的各種景色,經歷風雨。
-
做為一位母親,感知到孩子的好奇心與想像力:那種生命原初,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家庭、學校、社會制度上的控管、壓制與支配—我們的教育體制是怎麼一回事?」為人父母時,很清楚地看見,整個學校體制、內容的設計,都是一種規訓:一直在制約、壓制孩子。
-
做為一位藝術家,在板橋435的在地長期駐村經驗裡,她發現藝術家們在進駐後,演生出從眾、異化,被支配的型態。
「相較於一般民眾走進社會、企業體制裡,藝術家應該是個體性比較強烈的,可是在公部門管轄的藝術聚落裡,卻形塑出某種集體性。這凸顯了社會在資源分配、支配的權力關係的問題。」
「同孩子被權力關係支配一般,在地進駐後,又見這個問題。」瑋倫說:「我的心中,因此逐漸形成了具體的問題意識。」
-
作為一位研究者,因對教育抱有疑問,開始爬梳教育的發展歷史。始於駐村期間的工作坊,這時也開始以實驗性的方式進行。
A.P.D計畫:培養皿是觀察偶發的實驗現場。
細胞間的突變、互噬、
繁殖、觸發,相遇,相愛相殺
「從繪畫、雕塑進入畫廊的銷售系統時,我在思考:當創作進入類資本的循環,在當代除了銷售,藝術家的創作到底對於社會、對於整個環境,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藝術家能不能扮演這個角色?藝術家的協作有沒有一種力量,是可以給出不那麼陽性、單一敘事,或單一權力的東西?」
-
「拒絕異化與自我精神麻痺,我想要喚醒一些事情。」
以藝術創作的共感,達到溝通的目的。
創造一個可能對話、交流的介面。
-
「創作生產,來與大眾溝通我們的問題意識。從個人擴展到社會,我們必須去了解社會,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他人。」瑋倫說。
若面對個人,創作是藝術家聚焦於自身的反思過程,那麼A.P.D.計劃則是反向以一種全敞開的姿態,嘗試透過藝術聚落內部的動能,搭建起與其他社群之間的超連結網絡。「培養皿」的原初概念,便是希望翻轉從機構、企業為主體的專案形式,回到藝術家主體主動創造藝術對話的實驗現場。(摘自《上學趣》)
A.P.D. 計畫與島居
最初透過竹圍工作室得知日本藝術家武谷大介所發起的 <校外。教學 | 亞洲連結藝術創作計畫> ,當時在腦海中浮現的是西太平洋、東亞島弧上島嶼國家羅列的視覺意象,很想知道在此計畫執行的五年間,旅行的書包承載了哪些來自藝術家的觀察和關懷在我們這個島鏈上旅行,又是如何透過工作坊和在地的孩子們展開對話。
竹圍工作室從臺灣經驗出發,提出「島居:海島子民的N種永續生活」為切入視角,邀請藝術家針對「環境」、「教育」、「社會關係」、「臺灣與東南亞」四項議題進行創作發想,而A.P.D.計畫受邀處理是「教育」這個子題。
日本科學家中村修二曾提出對東亞教育的觀察中提到,東亞三國(中、日、韓)都是在19世紀末追趕西方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移植了西方現代教育、也就是源自普魯士的教育體制。「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裏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
無論是西方工業革命時期、亞洲追趕現代化的腳步,教育是作為上位者、統治階層用以馴化、調校人民為國家所用的手段工具。而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亞洲國家,正如中村修二所說「亞洲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於是,透過教科書內容設計和考試制度,搭建出國家教育體制的遊戲規則。教育本應建立在對於人獨立思想上的啟發,卻在政治或資本的運作下,提早異化人最細緻複雜的多樣性。更甚,則是在帝國殖民歷史中,作為思想改造和控制的工具。
(摘自《上學趣》)

珠媛
「那天我們一起去的。
從陳界仁的聲音裝置《迷向屋》出來後,珠媛哭了。因為在長期關注韓國慰安婦議題的情況下,她知道那時,她們就是被囚禁在這樣的小房間裡,充斥各樣噪音,狹窄無光。」「進入這個空間,身體感受會讓你直接地觸及到。」瑋倫說:「我覺得這就是藝術的力量。可是當代藝術到底能不能將這個『共感』做出來?讓人們可以去突破他原本的認知?」
-
珠媛也是北藝的學生,是韓國人,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她嫁給韓國先生,兩人都是全球化時代的流動人口,不過,他們屬於布爾喬亞式的高級流動,小孩在臺灣念美國學校。現在移動到新加坡,也都是要找最好的學校。「通常這樣家庭的父母,因為已經擁有足夠資源,所以不會有太多左派思想,不需要反思。」瑋倫說:「但她是個創作者。作為一位藝術家或作為一位創作者,你就會產生你的問題意識。」
-
一四年四月十六,韓國世越號沉沒事件,對於身為母親、同時會產生問題意識的創作者來說,是一個很強大的衝擊。「政府怎麼會有權利罔顧孩子們的性命?」珠媛於此同時,開始逐步地去了解:整個韓國政府國家民主化的歷程是什麼?瑋倫解釋道,因為臺灣跟韓國的民主化歷程是非常接近的。臺灣的美麗島事件、二二八,到韓國的光州事件,其實是並行的。於此階段,瑋倫與珠媛在針對臺灣民主化跟韓國民主化進行討論之餘,也探討民主化歷程:「對於我們這一代跟下一代,產生了什麼分裂上的想法?」
「我們這一代的中產階級普遍親藍。當有這個問題意識時,會去思考說:『那我要跟我的孩子說,你是中國人,還是你是臺灣人?我們的上一輩可能就沒有疑問,是中國人;我們下一輩的教育則是臺灣人。」瑋倫提問道:「那1980這個世代的我們,是誰?我們該怎麼教?』」
「所以很有趣地,我跟珠媛的對話從這開始,慢慢延伸,後來找了流水生,因為香港的事件又延燒了起來(水開始滾)。」
流水生
Maggie是在臺灣長大的香港人。
「從前聽父母講述大逃港經歷,我是沒有辦法理解的。」她說:「他們都在上海出生。那時正值文革時期,他們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從上海逃難到香港:我爸坐火車,我媽乘船;不論哪條路線,過程都非常驚險。就這樣,他們到了香港,因為工作認識彼此、相愛結婚,誕下我哥與我。」
香港從前作為英國殖民地,一直都是比較國際性的;Maggie的爺爺奶奶在軒尼詩道開了間上海館子,經營了三十幾年,直到父親那一輩沒有想要繼續經營,就收掉了。
Maggie父母在有了哥哥跟她之後,決定要創業。在臺灣剛起步時,他們舉家移民。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她在臺灣成長、念書。只有逢年過節,會回港探親、看看朋友。
而在Maggie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政治立場一直都偏藍。
-
去年反送中的事件,讓她產生了很大的自我反差與矛盾。她回憶,在臺灣三一八太陽花運動時,還沒有太多關於抗爭與民主這方面的連結。
香港反送中事件在前年三月份慢慢形成。五六月時,新聞媒體報導頻繁。
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有一群香港的年輕人被警察毆打,這讓Maggie非常震驚,並且憤怒;因為警察在她的印象中,應該是保護人民的角色。「那時,他們毆打的很多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學生,突然地我意識到:『我家鄉的人正被傷害。』」她開始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產生疑問。
很長一段時間,她都在推敲自己在臺灣、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聯:該如何看待「我」在這之中的位置?從六月開始,Maggie就一直在關注反送中事件,直到九月份開學,她看見學校美術系門口出現看板:一個學生參照反送中文宣海報畫出來的看板,之後她加入了學校裡由部份香港留學生組成的關注組。
「我那時在想,我到底該用什麼方式來聲援香港。」Maggie說。
-
「流水生的第一個展覽在當代藝術館,是由我們的指導教授黃建宏策展的。那時距離反送中運動爆發,將近半年。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民主運動。整個過程,我跟流水生另外兩名成員不斷地討論。」
Maggie解釋道,反送中運動與之前的雨傘運動很不一樣;這次主要理念是無大台—沒有領導人的狀態,每個個體都是大台,人們因為共同的信念,透過網路社群連結在一起;如果沒有網路社群,這些人是無法一起發聲的。
任何想聲援香港的人,都可以透過一個名為telegram的社群,在群組「文宣谷」裡,上傳反送中文宣。「那時我們收集的所有文宣,都是從文宣谷裡download下來的,從六月一直到十一月份的展覽。而這些只是其中一部份,因為有太多太多了。」
「許多港人用各種方式介入這個運動,製做文宣並分享出去。連結不同身分、不同職業、不同區域的人聚集,所以我們才會看到,為什麼一瞬間,會有一百萬人、兩百萬人出現在街頭—是靠社群媒體。在籌備展覽的期間,我跟另外兩名成員不斷地在分析,每個月每個月,出現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我們在研究:為什麼在事件爆發後,站出來的群眾會這麼多。」
信念最重要,我們不是在做一個藝術品
一九年十一月,展覽開始,而運動還沒結束。流水生的成員們無法掌握後面會發生什麼事,仍持續地吸收來自各方的新聞資訊。
-
「展覽結束後,黃建宏教授接著策畫了臺灣與光州的雙年展,他們希望『流水生』能不斷地演化下去,在關渡、光州美術館一起展覽,將香港民主運動的訊息,傳遞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那年反送中爆發,一些韓國藝人表態支持香港,其中一位藝人甚至親自到香港,用行動來聲援。「因為這與他們曾經的民主運動息息相關,他們都經歷過。」Maggie說。
流水生團隊在關渡美術館展覽時,進入到另一個階段。已經不只是純粹在整理出現過的文宣檔案。「前次我們download了大量的文宣,因為時間很趕,並未與製作文宣的藝術家交流。而這次在籌備時有一段製作期,有更多時間思考,我們發現:
力量能集結一起,是憑藉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反送中運動中出現了一個名詞:「手足」,在抗爭中互不相識,卻因感知到對方守護香港的意念,背靠背掩護彼此,交付性命。
「那種情感、信念是緊密並且強大的。」訪談到後來,我們都哭了,為犧牲的人們,為手足令人動容的情感,為了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直至今日,我仍記得那時她堅定的眼神。
目前仍在持續抗爭,我會跟著這個運動一起走下去,
一直支持下去

一九年六月十五,一名身穿黃衣的男子,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後,爬上金鐘太古廣場平台外,掛上「反送中 NO EXTRADITION TO CHINA」抗議標語,與警消人員僵持五小時後,墜樓身亡。
-
「這件事令我感到很震驚。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是為了香港跳樓自殺。」Maggie說:「那時,我心裡產生了一個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在先前的印象,香港與臺灣的年輕人給我的感覺不太一樣,香港人從小就學英文,吸收很多國外資訊,所接觸到的工作、文化都是很多元性的;臺灣雖然比較單純,卻也相對封閉、單一。香港的年輕人談吐各方面相對自信。所以在香港遭受壓迫時,他們反抗的力量會讓我感覺到:哇!那個爆發力是從來沒有看過的,他們被政府打壓,從一個這麼自信、自滿的狀態,打壓到一個我無法想像的地步。」
Maggie介入這個運動時,是非常地堅決:「我一定要持續地追蹤這個運動,最後看它是到什麼樣的程度。因為到現在我們都還不能說;這是一個還沒有成功的運動。」
「目前仍在持續抗爭中,我會跟著這個運動一起走下去,一直支持下去。
另外兩名成員也是。」她認真道。
身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在群眾中會找尋到什麼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至今我還在尋找。但這個定位會越來越清楚。」Maggie認真道。
-
去年的929臺港大遊行,是她參與的第一個遊行。
那天與會的人眾多,何韻詩也有來。
「那天起,我開始尋找我在這之中的定位。展覽透過網路社群,讓我更清楚這不單單只是一個工作;像人們每天上臉書一樣,任何文章po出去,你已經有一個位置了。
我的臉書po了很多與香港有關的訊息,一方面希望透過資訊媒體,讓更多人知道;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回饋:我發現臉書少了一些族群,發現讚數越來越少—這是種社會現象。同時我也會去思考,為什麼臺灣有一部份的人是這樣子,一部份人是這樣。」
經過反送中事件,族群的隔閡擴大,Maggie與她的家人也是。家裡親中,只有她一個人真的站出來,聲援反送中。「我只能盡量避免與父母提到香港的情況與立場。」她說:「直到今天,我都不認為自己是真的有參與到政治活動—我認為,我只是在強化自己的意識。」
「兩代之間的分裂在香港出現的狀態是更加地劇烈,有很多年輕人因此與家人鬧翻,都不回家。溝通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瑋倫所說:『教育是對下一代,產生認同與價值觀。』
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有下一代,我是不是也沒辦法跟我的下一代溝通?」
「但總會比過去來的好,會開始慢慢形成一個穩定的狀態。譬如臺灣的轉型正義,大家開始會有共同的意識,雖然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一定要給彼此一些討論的空間,溝通是最重要的。」

集體意識
1997香港回歸中國。
大量中國人流動到香港,對香港的醫療、居住、工作環境產生影響,改變了生活型態。尤其在政府又推出了什麼樣的政策,長久以來積壓內心的不滿不斷累積,直至爆發。
一四年傘運後,人們沉寂約有五年。許多參與反送中的人,是當時參與過雨傘運動的群眾,傘運後那幾年的時間是非常地消沉,甚至有很多人想不開,因為他們已經對政府失去信心了。
一九年反送中爆發之時,人們決定奮不顧身地站出—因為如果你再不行動,就沒有任何機會了。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而且很多人受了年輕人的影響:「為什麼會有十二三歲的小孩勇敢地加入?他們怎麼會了解什麼叫民主?為什麼他們會比大人還勇敢地站出來?」
Maggie感嘆道:「我為此感動地不得了!這麼多陌生人一同走上街頭,這麼多因素讓我感覺到,那就是『共感』,非常強烈;即使身處在臺灣我都能感受到:有很多人感受到共感的時刻,人們正積極地在聲援香港。」
-
「現在大家都用手機跟電腦,那很像一個安全的觀景臺。」瑋倫說:「Somehow我覺得在2020臺灣也是一個觀景臺:全世界這麼混亂,但我們還可以置身事外。西藏的問題…蒙古的問題…2020的各地。」
「當人們對他人遭遇的苦難漠不關心,就是一種冷漠。我們期望藝術品、藝術計畫,能喚起人們對於周遭環境、整個世界局面的關注跟理解—懷抱著希望事情可以更好,不再以置身事外的態度觀望。」
「現今的新聞資訊媒體發達,人們可以很快地知道世界各地發生了什麼,各種議題、災難。感知度也許會因為看得太多,反而麻痺。」Maggie補充道:「這也是我們這時能去思考的一個問題:究竟網路媒體所帶給人們對於事件的看法,到底是處在什麼樣的狀態?」
聚焦認同:不會只有對立的是與非,我們該走出一條新的路
「沒有對與錯,回到對與錯即為對立。臺灣應該要有一條新的路。」瑋倫說:「不是說:噢!我是藍是綠,是中國是臺灣,永遠都這樣去思考事情,這沒有新生成對這個島的一個想像;我們回到一個普世價值:如果要談人權談民主,應該講接下來的認同—是要下個世代慢慢去長出來,而不是我們告訴你們,我們的認同是什麼。」
-
2020年,中共面對新疆、蒙古實施的思想控制、語言滅絕,北韓對於境內人民資訊封鎖和官方意識形態輸入,都是人類歷史的一再重演。 在深受殖民歷史影響的台灣,現代化教育起源也曾經歷類似過程。日本殖民時期,積極推動皇民化教育,至1943年底,台灣兒童的義務教育普及率為71%,全亞洲只低於日本。二戰之後,國民政府在台進行威權統治,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校園充斥的是高壓、噤聲和思想箝制。
直到90年代隨著解嚴而起民主開放的政治氛圍,台灣才開始經歷一連串的教育改革。並逐步對於本土化、台灣主體意識、轉型正義等議題得以被納入國教教材內容。殖民歷史和政治介入,掌控著人民接受教育馴化的方向,長期下來形成不同世代間更大的認同斷裂。而填鴨式教育、功利升學主義,缺乏批判性的思考訓練,更僵化意識形態的固著,形成同溫層之間更難以相互傾聽、理解的鴻溝。
因此,當我思考如何回應「島居」和「永續」的策展概念,並以「教育」為支線的主題時,希望回到對於「教育制度」的反思。在島居的工作坊及作品籌備過程中,我邀請韓國創作者朴珠媛 (Park Juwon)一同加入,由於珠媛和我同為身帶母職的藝術創作者,我們從國民義務教育為題開始交流想法,進一步發現同處於1970-1980出生的我們,在韓國及台灣極為相似的民主化歷程中,面對光州事件、二二八事件,都曾是沉睡的國家信眾,不帶懷疑地接受教育和規訓,以單一視角認識自身歷史和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直到來自孩子們的提問,喚醒我們看見教育制度本身的陷阱。
即使身處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今日台灣和韓國,「教育」仍是國家、整體社會結構塑造集體認同和世代記憶的手段之一。如果歷史是屬於勝利者的書寫,至少我們要能掌握普世的核心價值、明辨是非的能力。孩子們即便對政治議題冷感和不理解,但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卻有著本質上天真、純粹的認同。受管控的教育輸出如同當代受監控的媒體,是對知識和現實世界理解的高牆。我們相信孩子們的開放性、對世界餘熄尚存的好奇心,由人性出發的天生共感力尚未被現實擠壓到心海深處,只消輕聲呼喚便會傾洩而出。
因此,我們在工作坊中,以民主、人權與教育為題,也邀請2020年在關渡美術館、光州美術館展出的「流水生」團隊成員Maggie Chang,一同參與基隆高中學生的工作坊,透過藝術家的視角與孩子們一同進行討論。
(摘自《上學趣》)
展出作品以《上學趣》小書,爬梳A.P.D.計畫
有興趣的人可以繼續觀看
不斷分裂、融合。再分裂、再融合。
在意識到我從來都是個完整的人時,渾身的細胞都在顫抖。
希望你們也能擁有此刻的感受。
那是生,在呼吸的一吸一吐之間—的此刻。
這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