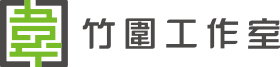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 Login to post comments

儘管深具成為「步行城市」的潛力,作為世界車輛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的澳門,絕非一個對行人友善的都市,據官方公佈的數字,澳門平均每公里道路的機動車輛數為550.9輛,遠遠超過國際上每公里200輛為臨界飽和點的規定。狹窄的單行車道緊鄰只容一人通過的人行道,許多路口並不架設紅綠燈,常常必須與汽車對峙才能抵達對街,澳門人與台灣人一樣大量依賴機車與汽車代步,藝穗節的城市漫遊在寸土寸金分秒必珍的澳門,儼然是窮人與背包客不合時宜的文化奢侈。而澳門的公共文化設施,也早已淹沒於不斷擴張的商業空間、賭場與旅遊區之中,藝文工作者長年來唯有在都市叢林中打著游擊戰,事實上,澳門第一個重要的劇場黑盒「曉角實驗室」,就是曉角劇社於1988年房市低迷,工廠紛紛遷往大陸的時節,用湊齊的團費低價買下的一個工廠單位,自行改造並獨立經營至今,並與近兩年新成立的「窮空間」,成為這一次城市藝穗節唯二的兩個黑盒展演空間;身兼曉角劇社團長與民政總署節目策畫人的許國權(大鳥),則是藝穗多年來的重要催生者,澳門藝穗因此與台北一樣成為世界少有的「官辦民營」藝穗節。
公園裏的政治角力
即使是「官辦民營」,該有的麻煩還是沒有少。已經申請濱海碼頭作為演出地點的《記憶》因為就在珠海的對岸,演出前一天引起海巡署到場關切與民政總署出面協調,好不容易獲得演出的許可;而盧廉若公園的《異國‧異想》則因為公部門間的溝通不良,舞者礙於公園館內同時進行的展覽,不得不移到戶外石磚地演出,但同一時間進來公園參觀或運動的市民,也不願意在一個對民眾開放的地方購票進場。另一個也在公園的《無處不喵》,更因展示了當地的流浪貓照片並標示了牠們的出沒地點,同時招致愛貓人士與反貓人士的投訴,前者認為標示貓隻出沒地點威脅了流浪貓的生存,後者認為流浪貓照片的展出,變向鼓勵流浪貓的存在,展覽最後只好被迫轉移至獨立藝文場所「貓空間」。然而,這些爭議雖為這個鮮為人知的小眾慶典注入一定程度的關注,卻也雷聲大雨點小地難以引起澳門人使用公共空間的討論或思辯。事實上,若非藝穗節的舉辦,澳門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平日其實也難以取得這些場所的演出權,倘若我們撇開公部門間的權責分工問題,這些在台灣與澳門劇場史、公共藝術史上屢見不鮮的「公共性」爭論,對照於今年新北市環境劇場藝術節與台北藝術節發生的爭議或衝突(詳見破報復刊627期:《當劇場出現在你家隔壁-新北市藝術節環境劇場系列的挑戰》),更常常點出藝術工作者在與公部門短時間的合作中,因為缺乏對空間屬性、歷史甚或當地居民傳統價值、生活習慣的長期觀察和理解,作品既無法幫助社群意識的鞏固也無能挑釁顛覆,存在的只有溝通的斷裂。
李耀誠的靜行音樂會《一天九澳》對環境的運用也因此顯得彌足珍貴。為了尋覓一個靜謐的表演空間,策展單位與表演者繞遍整個澳門,卻發現處處都有城市的低頻聲嗡嗡作響,最後終於找到一個離山腳的水泥工廠有一段距離,平常不開放的「九澳水庫」及淡水濕地生態保育區做為演出地點。
一開始觀眾被帶到燒烤公園旁邊宣布必須遵守的事項─不能說話,盡量放輕腳步,不能進食,不能使用照明系統─我們於是在靜默中開啟尋找「音樂」的旅程。領路人以鐘聲提示著觀眾何時前進何時停止,集體緘默三小時步行於蜿蜒的山路。表演者時而佇立在前方輕聲敲打木魚、法器甚至樹幹,時而一邊演奏甘美朗一邊遠離佇立的觀眾,時而在被要求閉目的觀眾旁輕聲低語。漫長的步行宛若一種神聖的儀式,靜默則放大了所有參與者的感知,我們因此清晰聽見山腳或遠或近的中東鼓聲如影隨形,與所有的蟲鳴、風聲與遠處遊客的交談成為一個整體。
表演者顯然深悉該地地形,並長時間的用器樂與環境自然聲響對話,而這樣一個生態區的排練及演出若非官方的支持確也難以成行,志工們似乎也經過密切的排練,同時身兼放置樂器、協助引領觀眾的角色。但當我在漫長的步行中,聽見山腳下水泥工廠的運轉聲宛若循環音樂(loop sound)般隱現時還是不禁要想,除卻台灣這兩年時興在咖啡廳、公寓裏演出的沙龍環境劇,是否唯有這麼一個被都市噪音「驅逐」到偏遠山區的表演,才得以讓與空間充分對話的「環境劇場」作品成為可能?而就算今日對空間權力的衝撞與挑釁已非「環境劇場」所需承載的必要之「惡」,那麼在「藝穗」已成為各國城市文化品牌的推銷和比拼戰場的今日,「穗」(fringe)這個英文語境原初所帶有的邊緣和自發性意義,又該如何在創作者、民間與政府間的角力過程裏,找到具體實踐的作為和方法?受邀參與這一次澳門城市藝穗座談的上海草台班,或許還能作為重要參照。
(圖片為石頭公社的吳方洲在黑沙海灘上,用輪椅推著模型豬與大海搏鬥的行為藝術《死裡逃生的秘密》,由澳門劇場文化協會提供)
.本文摘錄自《破報》副刊6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