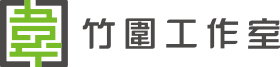創藝評論
詹偉雄/文創發展 根本不需要政策
經常受邀參與文建會或經濟部相關討論的詹偉雄,自嘲常被派去做政府輔導民間企業的老師,但講話都很烏鴉,「我都說應該要去跟人家學,怎麼去教別人,人家是創業家,在社會上一定有他自己的能力」。真正的文化創意產業,在詹偉雄定義是,「能用新形式創作出新意義」,Apple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文創發展,根本不需要政策」。
藝術外一章-從寶藏巖看城市文化特色
城市間的競爭,不只比硬體,也要比軟體;要比適合居住度,比特色、比風格、比文化底蘊、比文明尺度,甚至比歷史城區復舊的完整度及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程度。在高度追求建設而變得過於嚴謹又一致性的城市中,對於老舊或創意街區的改造或維護,可以成為一個城市是否適合居住,讓居民可以感到輕鬆、自在與愉悅的關鍵,甚至是大家在繁忙緊張的都市生活之餘,有個緩慢節奏的心靈處所。
國藝會不能企業化
文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是相關卻不相同的兩件事。政府立法獎勵藝術,是因為嚴肅的藝術不是可以賺錢的產業。而文創幾乎與大眾文化相通,常常是由企業主導的。如果利用國藝會有限的那一點利息,補助可以吸引投資的大眾性藝術,國藝會的存在價值就值得懷疑了。藝術家如果每天腦筋裡只想到如何賣,還會有劃時代的作品出現嗎?這是常識,大家心裡都明白。
展能藝術的美學與政治
看多了不一樣的演出,我開始瞭解,其實很多藝術家所追求的「精準」,在這邊是不適用的。「精準」絕對不是藝術唯一的標準或訴求。我們必須打破這樣的既定觀念。像是視障人士的肢體動作,可能會比較緩慢,因為他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使身體定位,透過放低重心來尋找信任感、發現節奏感等等。過程中,更需要大量的摸索與探觸,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就會讓「身體感」被發掘出來。例如耿一偉的作品《守墓人》,就善用了這一個過程,透過一種方式,讓盲人身體的緩慢特質,透過藝術的手法將其合理化,讓「合理化」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產生。
消毒池,未曾消失──談台北美術獎作品「樂生我家」消毒爭議
承辦這個競賽展的北美館展覽組研究員蕭淑文表示,那並非改制後的規則,「那是因為我做的!我希望給藝術家最好的support。」也因此她對陳潔晧在開幕記者會上向媒體反映北美館要求樂生物品消毒一事相當不滿,「如果美術館真的這麼官僚,他可以擺那些東西在那邊嗎?而且所有這樣的執行,我們會協助嗎?你認為那些東西是他做出來的嗎?是我們協助出來的。」而陳潔晧則表示,此次比賽簡章有寫「參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內協同卸佈展,本館將提供相關協助」,他認為如果這是公開且公正的比賽,比賽簡章應該明確說明美術館和比賽者的相關義務與責任,而非任何幫助都是對藝術家的恩典。
背向未來的天使-從十年回歸到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節(下)
澳門的公共文化設施,也早已淹沒於不斷擴張的商業空間、賭場與旅遊區之中,藝文工作者長年來唯有在都市叢林中打著游擊戰,事實上,澳門第一個重要的劇場黑盒「曉角實驗室」,就是曉角劇社於1988年房市低迷,工廠紛紛遷往大陸的時節,用湊齊的團費低價買下的一個工廠單位,自行改造並獨立經營至今,並與近兩年新成立的「窮空間」,成為這一次城市藝穗節唯二的兩個黑盒展演空間;身兼曉角劇社團長與民政總署節目策畫人的許國權(大鳥),則是藝穗多年來的重要催生者,澳門藝穗因此與台北一樣成為世界少有的「官辦民營」藝穗節。
背向未來的天使─從十年回歸到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節(上)
回歸十年的第十屆澳門城市藝穗節(fringe),就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首次訪澳視察,參加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一年一度的格蘭披治大 賽車與行政會公佈明年現金分享計畫金額的11月間「悄然」展開,儘管大型Banner依舊在各旅遊熱點豎起,但藝穗節的相關消息顯然淹沒在這些重大事件與 活動之中,遲至開幕演出前一天才出現時間錯誤百出的傳單,演出開始後才出現的節目冊,凸顯澳門官方對該節日的輕忽。然而,不管政府的關注或資源挹注多少, 澳門的劇場界卻也還是不甘沉默,從團隊自行印製DM到口耳相傳、獨立經營的藝文空間、刊物和網路訊息的互通有無,一年一度的澳門藝穗節依舊凝聚一小群圈內 人與藝文愛好者。
談藝術政治前,讓我們先揭開內部經費的大餅-《破報》再訪2010台北雙年展
台北雙年展走到現在第12年,從上一屆向著政治藝術,歷經這兩年來北美館與國美館引爆的各種文化體制風風雨雨,決心要轉身先過來面對「藝術政治」。如同前任館長、現任文化局長謝小韞所說的,這次2010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10TB)是「挑戰了承辦單位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勇氣與作為」,這次的兩位策展人企圖回觀「藝術的製造、消費與流通」,於是出現了白雙全的《回家計畫》和《儲物箱》、石晉華的《台北的X棵樹》和《當代藝術煉金術四部曲》、Christian Jankowski的《館長剪輯版》或者Burak Delier的《「我們必將勝利」調查》等,觸及到藝術形而上和形而下兩個交結點的作品,當然還有饒加恩胎死腹中的《夜間雙年展》計畫,只存在於導覽手冊中的兩頁,更是以絕對幽微的方式,指出了策展人面對官方機構行事的困境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