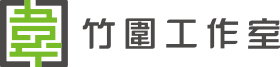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 Login to post comments
作者:于善祿
汪其楣: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于善祿老師到課堂上,來和我們分享他這幾年參與展能藝術節的觀察和經驗。于老師也是北藝大戲劇系的老師,我們非常難得能邀請到這麼一位看戲經驗多元又豐沛,觀察深入而觀念活潑的老師,請他就特殊藝術的表演和他個人的觀察來課堂上分享,以補充我們經驗上的不足。我們歡迎于老師。
拒絕猴戲
于善祿:
首先,我要舉一個比較不好的例子。這是在2004年左右,我欣賞了「美力時空」這個團隊的演出,整個過程中的一切都讓我很不自在。我們都知道馬戲團,是透過馴獸師運用聲音、道具、食物,來馴化野獸,讓牠們演出。而在這個作品裡面,他們運用喇叭聲來發號施令,讓每個身心障礙演員繞場,似乎在「展示」每個演員的身心障礙狀態,配合著國外馬戲團的音樂。我不禁懷疑,我們是在看一群身心障礙者耍猴戲、扮馬戲嗎?到了演出結束,還當觀眾的面前,發給演員一人一個如糖果包的禮物,難道他們真的就像海洋世界裡的海豚一樣,在表演到了一個階段,馴獸師就要給一條魚嗎?藝術指導和身心障礙者之間,成了馴獸師與動物的關係了嗎?成了發號施令與接受刺激的動作制約關係了嗎?這樣還有所謂的藝術創造性嗎?
當然,好的例子也不是沒有。台灣的特殊藝術其實不是從近十年才發跡的,事實上,陸陸續續一直都有人在做。我的碩士論文主要是研究七○年代的台灣現代戲劇發展,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劇團出現,就是汪其楣老師創辦的聾劇團,透過特殊的方式跟演員進行排練和演出,一直到現在都還持續著。
就我的經驗而言,在台北地區,一開始我們比較能看見的身心障礙表演,主要是王墨林老師的身體氣象館;一直到後來的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其中是以視障居多)。從第一屆開始,也有一些聽障的朋友加入,像是跟台北聾劇團合作的演出等等。
身體氣象館 (Body Phase Studio),是1992年成立的,根據江世芳的文章,他們一開始的宗旨只是「想要考驗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國際化』、『多元化』了」。後來他們引進了一系列身體文化、行為藝術等活動,發展為一跨文化的藝術團體。另外,還策劃一年一度的「國際跨文化身體表演藝術節」,不斷與歐美、亞洲等地的前衛藝術家進行國際性的、實驗性的表演藝術交流,推薦年輕一代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到布魯塞爾、馬賽、東京、香港等地參加藝術活動。
而「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就是由身體氣象館主辦、牯嶺街小劇場協辦的系列藝術活動。內容包含視覺障礙、肢體障礙、聽覺機能障礙、智能障礙等不同障別的表演節目。「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舉辦多年以來,除了將外國的展能藝術引介到台灣,也開辦身體與表演的工作坊,讓視障演員與不同領域、地域的藝術家們進行交流。
到後來,藝術節打開了名號以後,漸漸地也有國際團隊加入演出,其中以香港團隊居多。
這些活動中的靈魂人物就是王墨林先生。在台灣的藝文界,一提到王墨林,不同的人會有不同反應,也會想起他大聲疾呼的身影;而他在大聲疾呼時所使用的語言、意識形態、美學觀點,甚至政治立場,都使他顯得十分突出。無論如何,不容否認的是,王墨林先生長期對小劇場、身體文化、表演藝術、行為藝術、前衛藝術等等議題的關注,已經形成台灣藝文界一道極為重要的風景。
活著,就是活著,不要區分看得見或看不見
最近我去觀賞了牯嶺街小劇場的「暗中有戲工作坊」表演呈現。他們有個作品叫做《在視與不視之間》,裡面的演員主要有十位,其中約有兩位是沒有經驗的,其他都是有經驗的演員。這回我花比較多的時間去觀察「有多年劇場表演經驗的學員」與「經驗較少或初體驗的學員」的身體差別,包含:對空間的判別力、安全感、方向感等等;看得出來經驗較少或初體驗的學員在這部份需要努力的地方還很多。至於有多年劇場表演經驗的學員裡,我發現有兩、三位感覺很「油」,但卻「油」得很幽默、可愛,像劉懋瑩就是一個例子。
在內容上,呈現的都是視障演員生活中的片段。而在劉懋瑩的片段中,呈現出來的是很詩意的感覺;加上他很喜歡閱讀有聲書,因而即興說出了一些詩意的言語與片段。觀眾本來可能會以為:又是一個普通的片段演出,但結果卻呈現出一種詩意的氛圍。也因為他的表現,就帶起了其他演員「言語上的甦醒」。在表演結束後的觀眾分享中,更因為這樣詩意的氣氛,大家玩起一種詩意的語言遊戲,雖然我覺得有一點點「噁心」(我的意思是「過度浪漫」)—那一場演出後的座談會,主持人請大家用一、兩句話來發表觀賞心得。就是因為劉懋瑩帶頭講了一些詩情畫意、過度抒情的語句之後,那樣的語句就開始像傳染病一樣,在群眾間互相感染。比方說:我今天晚上在這裡感受到了春天的花蕊……類似這樣子的語言!正當大家開始說這種「噁心」的話時,我也舉了手,說:「活著。」因為我不想像他們那麼「噁心」。「活著」,就是表演中的當下身體狀態,也就是一種身體和外在的關係:比如身體跟地板的關係、跟牆壁的關係,或者是和其他夥伴彼此摸索的關係等等;藉由這樣的關係,再回去確定自己身體的存在感。所以我當晚的感覺是:活著,就是活著,不用區分看得見或看不見。
在視與不視之間
《在視與不視之間》的第二個表演片段,主要演員是包含廖燦誠在內的六位盲人演員,與六位明眼的陪伴員。由廖燦誠帶隊,後面跟著六個盲眼的夥伴,他們要去喝咖啡。但在他們前方的場中央,擺了好幾張塑膠板凳,要是他們直直走的話,就會撞到這些板凳—藉此來象徵生活中的障礙空間。然後陪伴員出場,他們必須搶先盲人們一步,把塑膠板凳拉開;當盲人們想要坐下來,陪伴員就要立刻把椅子遞上。這些橋段的象徵意義當然是很明顯的,就是指向一個「無障礙空間」,指向一種盲人想像中的理想生活空間,就是當他們走在路上的時候,所有的障礙可以被直接排除。另外還有一段,是一位學員拿著白手杖站在台上,而其他人在旁邊說著一些對白,說了大約十分多鐘,內容主要都是一般人對視障的刻板印象。最後該演員走到台邊,唱起〈你是我的眼〉,歌聲渾厚並帶點滄桑,令人聽起來非常感動。這首歌很耳熟能詳,但在一般狀態下聽,和擺在黑暗的脈絡下聽,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我講這些演出的原因是:其實這些演出都可以達到一種詩意的昇華。同時,有些幽默的片段也是視障者在生活中常見的。比如說,有個常來吃麵的客人,跟弱視的麵攤老闆娘說:「老闆娘,多加一顆滷蛋。」但老闆娘因為弱視,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加了一個滷蛋,又多放兩塊叉燒。客人便說:「妳多加了兩塊叉燒啦!」這時老闆娘就說:「沒有啊!那就是滷蛋啊!拿去吃啊!」類似這樣的橋段。這裡面有一種幽默感,就是老闆娘弱視,滷蛋、叉燒都分不清楚;同時又有一種人情味存在,因為我們不知道老闆娘是不小心多放了叉燒,還是故意要請客人多吃一點。
幽默不全然是好的,也有一些糟糕的例子。最近,蕭煌奇提到三立電視台《天下父母心》的內容。他說:「劇中的盲女蕾蕾一角,被老公的情婦欺負,甚至情婦和老公在她眼前偷情,她都渾然不知。看到這樣的劇情我是氣到想吐血,這劇情這樣灑狗血,簡直把盲人都當笨蛋了!」
這個誇張的劇情,讓我想到伊底帕斯 (Oedipus the King) 這個劇本。劇裡的盲人先知泰瑞西阿斯(Tiresias)看得清事情,但明眼的伊底帕斯卻看不清這一切。這個情節呈現了一個很明顯的衝突。其實視障只是「弱能」而非「弱智」,這是引用自香港那邊的概念,我很喜歡這樣的概念。一旦認為身心障礙是一種弱能,那麼他們在形容特殊藝術時,就會用「展能藝術」這樣的名稱。因為弱能,所以可能會遇到一些障礙,但是也可以延展能力,用藝術的方式去呈現;這樣的話,藝術就沒有疆界,真正達到「藝無疆」的境界。
「精準」不是唯一的審美尺度
在第一屆(2001)的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節時,我也和一般人一樣,用一種獵奇、驚訝、特技、慈善等等的心態去看演出。可是我很快地就發現,這東西不應該是這個樣子。那一年他們請了一個法國的團隊來跟新寶島視障者藝團做工作坊,他們彼此之間雖然在語言溝通上有困難,但卻找到一種順利溝通的方式,就是用音樂與舞蹈來克服。那是一種身體的訓練,屬於接觸即興,同時播放音樂,然後大家去感受那個音樂的情緒、節奏,在這之中可以是盲人和明眼人的互動,也可以是盲人跟盲人的互動。演出後的座談會上,有觀眾問盲人表演者們,如何知道舞台的方向?如何確認走位?其實他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貼地線,要不就是肢體接觸,或是在舞台的兩側用手發出聲音,在這些簡單的提示之後,表演者就知道要退場或走位的方向了。他們也常常用滾動的方式來退場,讓身體的重心和地板貼在一起,這樣就不怕跌倒,可以慢慢滾到舞台的兩側。此後我每年都會去看,也對表演者使用不同的方式在舞台上定向、移動感到好奇。
看多了不一樣的演出,我開始瞭解,其實很多藝術家所追求的「精準」,在這邊是不適用的。「精準」絕對不是藝術唯一的標準或訴求。我們必須打破這樣的既定觀念。像是視障人士的肢體動作,可能會比較緩慢,因為他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使身體定位,透過放低重心來尋找信任感、發現節奏感等等。過程中,更需要大量的摸索與探觸,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就會讓「身體感」被發掘出來。例如耿一偉的作品《守墓人》,就善用了這一個過程,透過一種方式,讓盲人身體的緩慢特質,透過藝術的手法將其合理化,讓「合理化」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產生。
耿一偉仔細觀察視障演員身體的若干特質,諸如緩慢、不「流暢」、不「精準」等等。因而他將懸絲偶的概念運用到這個演出當中,讓每個演員的背後都插上一組木製的骨架,就像是懸絲偶的操偶桿一樣,再用鬆緊帶,一端綁住演員的手腕與腳踝,另一端則與骨架相連,如此一來,幾可亂真的懸絲偶人就有了初步的外形設計,接著再將演員的肢體訓練成「偶」的感覺;甚至安排了兩個黑衣人(其中一名為耿一偉自己),造型和作用都很像日本劇場中的檢場,隨時可以上台協助演員(或者可以說「偶人」)的動作與方位。在審美的互動關係上,耿一偉的設計,將視障者在舞台的表演身體給合理化了。也就是說,所謂的緩慢、不「流暢」、與不「精準」,通通都具有了恰當的說服力,我認為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設計。
在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的許多作品內,可以看見明╱盲間的辯證,以及詩、樂、美的融合,一些乍看之下不相容的事物,卻在藝術創作中得到自身的內在合理性。我對展能藝術的審美經驗是:我可以看見展能藝術家的身體,與空間的對話,在那之間產生出精彩的能量,以及豐富的情感;同時,來跟觀眾進行溝通。
我記得有一個香港的作品,是謝偉祺的《閃:我的戲劇生涯》,觀眾可以看見從明到盲之間的變化,進而去體會到演員身體的記憶與感受;儘管有很多都是負面的複雜感覺,隨著演出,觀眾也能慢慢體會。藉著各種情感記憶、身體記憶,在參與演出工作坊以後,觀眾的人生或許就產生了改變。這個作品的結尾是開放式的結局,最後也提出了很多平常觀眾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問題,然後促使觀眾去思考、去重新體會。在這個作品的舞台上,有許多大型的黑色塑膠袋,其中一個裡頭藏了謝偉祺,他不斷地扭動與掙扎,也不斷使勁發出聲音,最 後終於撐破塑膠袋,象徵他從母體脫胎而出(但是他卻逐漸失去視力,十幾年前已完全失明)。他的感受是:「悲憂、悲愁、悲哀、悲傷、悲痛、悲喊、悲鳴、悲春、悲秋、悲日月、悲國、悲家、悲仇、悲恨、悲鬥、悲狠、悲天、悲地、悲人、悲萬物」(引號裡的文字,來自於謝偉祺撒向觀眾的滿場紙片,上頭所印的就是這些文字),即使他為如此多的人事物而悲,但最後他仍「但願……」,對這樣的世界與自己的人生仍存有希望。
謝偉祺以平易近人的第一人稱與觀眾建立關係,首先,他向觀眾表示:自己的普通話說得並不好(但我還算聽懂七、八成他的廣東腔),然後跟觀眾談起他失明的經過與失明後的感受,同時還提到他參與戲劇表演工作以來的心境轉換。有一個片段,是他在劇場裡頭問天、問神、問上帝、問菩薩、問先哲,但卻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回答他「世界為什麼是黑暗的」、「他為什麼盲了」等問題,頗有屈原問天、把天都問啞了的氣勢。最後,他習慣了在這個空間裡自處,找到了跟這個世界的相處之道。
像我們這樣的人,要指稱一個地方,可能會說:「就在那邊啊!」因為我們可以簡單地意會到「對,就在那邊」。但對身心障礙者而言,那或許是一種無限的方向感。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感覺,對別人可不一定。這很值得大家去重新思考。
「每一個人」,是包含「所有的人」,而不是只有我們習於見到的那些人
我要提出「不分」的概念。「不分」,原本是當代性別研究的概念,也是一本書的書名(女書文化出版,作者為「天空若藍」),而我把它借來形容對「傷健」的溝通與融合。「傷」指的是弱能人士,而「健」指的是目前身心健全的人(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我們大部份人都只是有健全的身體,而心態可能都有點問題)。身和心之間,其實可以從很多角度去細膩區分。而唯有不分,才能有更超然的藝術創作與審美思維。
最後,我還有一個小小的體會,就是「差異」。這是自然法則,是人(以及其他物種)天生就存在的。但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唯一,跟你屬於什麼障別一點關係也沒有。
反倒是人們常常會用教育的方式、規定的方式,來對世界進行標準化、統一化、制式化、規範化……的歸納,這種人為的途徑無疑是霸道與暴力的。既然如此,我們才應該要為每一個人創造平等的藝術環境。藝術屬於每一個人,不是嗎?也就是說:所謂的「每一個人」,是包含「所有的人」,而不是只有我們習於見到的那些人。我們必須把「一切」包含在內。這種「不分」的態度,既是最基本的,也是至關重要的。
展能藝術的現況
至於展能藝術目前發展的狀況,可以從下列幾個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就我所知,目前各種障別的展能藝術都有人在做。從這件事情的第一層意義來講,可以說這些團體提供了一些機會,讓各種障別的人,不至於一直停留在原來大家對他的刻板印象裡面。那感覺好像是說,我們提供了一個藝術的方法、藝術的管道,讓這些身心障礙者朋友有一個另類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或是抒發自己。這是第一層意思。
第二層意義是說,他們仍然必須面對外界的既定眼光。就像我一開始提到的,人們一開始接觸、面對這類作品時,多半抱持著一種「看馬戲」,一種獵奇的心態。他們勢必得面對社會的這種觀感。然後,他們怎麼接受這樣的社會觀感,然後進一步去延伸作品,還要扭轉那個形象。我所謂「扭轉形象」,並不是:「我是身心障礙者,我要來搞個特技秀,我可以跟明眼人做一樣的動作」。我認為並不需要這樣。而應該是去思考:「要怎樣才能把我的特質合理化?」就像剛剛我在談耿一偉的作品那樣。如何用藝術的方法,來把身體的特質給「合理化」,合理化之後再去昇華它—這大概就是展能藝術的意義。
至於台灣展能藝術現階段的問題,我覺得可能是在找一些公部門的資源上,會比較辛苦一點。比方說:他們現在要去申請一件案子,還是得和其他案子一起「被評比」、「被審查」,才有可能得到公部門的贊助。換句話說,不是每案必中的,還是得跟其他案子競爭;講難聽點,就是「評審不一定會買你的帳」。
另一方面則是:假設現在案子過了,可是實際補助下來的金額,只有當初提的預算的一半,那你還是得做啊!現在拿公部門的資源就是這樣,拿到補助之後,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完成。當然也可以把案子多投幾個單位,或是找一些贊助,然後把這些資源湊起來。不過對他們來說,找資源確實是比較辛苦一點,不僅缺乏行政人員,也常不被當做藝術團體來看待。
再來,在「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裡,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障別之間的交流,但在活動結束之後,或是平常的時候,我不知道各種障別之間還有沒有交流?「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是一個很好的代表,它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每年找來非常多展能藝術家,包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障別。但我的問題是說,如果2001年時,王墨林沒有辦這個活動,那他們是不是還能有這樣的平台呢?會不會變成:有能力的,可以找很多資源;不會找的,可能很快就散掉了?
很慶幸地,雖然「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每年都很辛苦,但還是堅持下來了。像2009年下半年,因為他們沒找到錢,所以改用工作坊的方式,找了陪伴員、老師去帶學員,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找了許多團體,辦成一個類似節慶的活動。他們換了一個形式,讓「第六種官能」這個概念,每年持續發生;但如果某一年活動停掉,這個概念可能很快就會散掉了。所以牯嶺街小劇場其實非常有心,就算再沒錢他們還是會持續下去,這是很值得我們去支持的。
【本文摘錄於汪其楣編著,《歸零與無限─臺灣特殊藝術金講義》,臺北:聯合文學,2010,頁14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