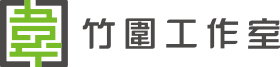採訪、撰稿/ 張姿婷
攝影/ 黃煒鈞

那日午後,金澤的陽光照映水面、岸邊植物、對面房屋,一切都閃閃發亮。欣姸與散步計畫的人們坐在犀川旁,和身邊的人分享一個回憶或故事。她與其中一位參與者,總結了在金澤駐村的心得,其實進行到最後她有點不曉得:「這個計畫到底是什麼?這算不算是藝術?」但她做得很開心。對方也是藝術家,跟她說:她也是這麼想的。

散步計畫對於欣姸來說,一直在變化。
一七年十月,她來到日本金澤藝術埠口(Kanazawa Art Port, Kapo)駐村,邀請了22人參與《與我散步》計畫,請他們個別帶領她走平時日常生活經過、或是充滿回憶的路線,並與她分享他們的故事。在赴約之前,她會以想像中對方的氣質為依據,準備一朵欲贈予參與者的花。
計畫的最後,欣姸借了一些對他們具有意義的物件,舉辦了展覽;除此之外,也藉他們的故事重新設計兩條路線,帶了小團的導覽,一次大約五個人。這次她偽裝成金澤的人們,譬如假裝她是一位媽媽,帶她兩個兒子的故事。


一九年二月,她在海桐中心第一次嘗試策畫召集的展覽《隱形風景》,找了幾位藝術家朋友回應《與我散步》計畫的某些關鍵字。
「那時我對於使用他人的故事感到恐懼,不確定能用到什麼樣的程度。」所以她設計了一條散步路線,全然地使用自己的故事,只是將地點置換成藝術中心附近的大龍峒。她說她爺爺的靈骨塔在這;從前姥姥帶她去吃了什麼;故事為真,唯獨地點是假。


一九年三月,進駐光州美術館的國際駐村工作室(GMA International Residency Studio),延續先前的散步計畫,這次她個別與16人散步。
二零年七月,臺北國際藝術村《找尋呼吸的路徑》出訪藝術家聯展,每周有一日欣姸會在展場,觀眾可以從一桌16個花瓶中選一支(其中3瓶沒有花),她會訴說那個人的故事,並引領觀眾到不同的物件前,講述在光州駐村的散步經驗。
「我將自己視為一個啟動者,如果你來,我可以跟你說那個人的故事。」
「我帶你到物件旁,跟你說:我第一次見到你,你怎麼樣、我們怎麼樣,做了什麼事。等於是直接地將你代入角色,變成你旁觀這個人的旅途,或是主觀經歷。我可能會問你一些問題,譬如:『你最近還有再去那個地方嗎?』『或是你最近好嗎?』」
今天兩個人來,選了同一個瓶子,故事也會因為回應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她會觀察參與者有什麼樣的材料,順著他講,故事因此產生變化。
-
故事對欣姸來說,是一種素材,也像個影子;最後都會回到她身上。
如何去運用這些,如何回應,如何再一次地與現場互動與故事重述,或是將參與者置入她所捏造的環境裡;直至今日,欣姸還在持續地實驗、玩耍。
而故事正不斷地變動。
臺北散步

都怎麼判斷遊客來自哪個縣市?
「在路上走的人,一定是從臺北來的。」曾被這樣調侃的她笑道。
「臺北是個很適合走路的城市。」欣姸說:「我是真的滿愛她。」
對觀光客來說,臺北似乎沒有哪是非去不可的景點。她解釋:「但如果在這生活一段時間,也許就能體會她的好。像是那些看似沒什麼的老巷弄、多到不可思議的咖啡廳。用走的,就可以到很多地方。」
-
「即使是離你很近的地方,也有不走那條路就不會看到的景色。」
她很愛走路,時常坐公車到某個地方,再從那開始。沒有明確的目的地。
這讓我想起那個會跳上區間車,隨意地選擇陌生車站下車,在那街道巷弄四處探險的朋友。
「好浪漫哦。」欣姸說:「我小時候想到很遠的地方去,也會搭公車,
但它是環狀的。
所以我就又繞回來了。有點悲傷。」她笑說。

欣姸現在住在母親小時候的家,她姥姥的家。父母是小學同學,家就住對面。
有天,父親也參與了她的《與我散步》計畫。
帶著她散步在家附近的路,講了許多她從沒經歷過的事:這裡以前是個水圳,那曾是個芭樂園之類。
那次父親知道要帶她去散步,很認真地準備了。
「這讓我感到很震撼。我跟我爸沒有不熟,感情滿好的。可是住在這一輩子,平時不會特意聊到這些東西:我從沒見過的,這個地方本來的樣子。」
「散步是一個滿好的方式,能讓我們重新去認識生活的周遭環境。」
「即使是沒有目的的散步。」
「一封給臺北的情書」

「我希望臺北不要一直被更新、更新、更新。希望它一邊很新,
一邊還是能將舊的事物保留下來。」
-
「採訪前的這個早上,我一直在想我要對她說什麼。」她認真道:「我平時有在攝影,雖然不是那麼直接地在記錄臺北;但這些影像的確是我累積在生活裡的痕跡。」
-
「有時我蠻怕設計的人。譬如說那些變電箱被漆成灰色,實在是蠻無聊的。」

不久前,雙連謙和市場西側的攤販被迫撤離。
作為中山大同傳統宗教與經濟文化中心的雙連市場,對於在臺北生長的欣姸來說,是很深刻的記憶。「我很常路過雙連市場,有時也會去那買東西。最近她因為沒什麼道理的決定,被弄掉了,雖然還剩一半啦。我本來就對都更很在意,理智上明白這是一個城市必然的過程,建築老舊勢必會面臨這個問題。」
她很擔心這個城市一直這樣更新下去,就不會有任何東西被累積下來。她認為一定有別的方式。建築是這樣,比起打掉重建,維護的工程總是要來的浩大、耗時也耗經費。
「我就是很愛臺北!希望她不用變得『更美』,現在這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