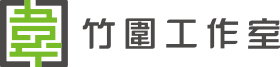採訪、撰稿/ 張姿婷
海風與笛鳴
坐落於山腰,從走廊望出就是基隆港。迎面而來的夏風挾著淡淡海的氣息。
連綿的雨,落在傍海連綿的山城;島居人們的故事沾著水氣,一頁頁濕潤。
基隆的山、海和雨,陳釀著她深厚的文化底蘊。
-
那日,中正國中一間教室,響起了許久未聞的公主號鳴笛,與孩子們的驚呼聲。
-
二零年六月十八日,依佩來到基隆中正區的中正國中,與孩子們探討「環境、海洋、藝術」三者的相關性與發現。
追溯十七世紀基隆港殖民時期歷史、中船路由來、基隆山和基隆嶼的位置;觀看影片《海洋有你》、《看見臺灣》的海洋劇照,播放海底生物、機器的聲音,讓孩子們重新認識海底生物、反思海洋的改變;依佩也領孩子們透過音樂來感受,如歌詠基隆從前繁華的《港口情歌》等。
並分享她在印尼亞齊的駐村經驗、《未來種子:熱帶雨林調查研究計畫》,最後她也邀請學生們在紙上畫出與海洋的回憶:復育珊瑚、路上造礁行動、淨灘與出海捕魚等,中正國中的學生熱情地上臺分享各自與海的相處經歷,然而除了愉快的回憶,同時也發現如今漂流、堆積在海岸的垃圾,是越來越多了。
-
全班25個小朋友,24個家裡是會講臺語的,唯一的那個同學雖然聽得懂,但不太會說;有時也因講得不輪轉,被班上其他同學取笑。中間下課時,依佩播了美秀集團的《電火王》,全班同學突然high起來。有趣的是,那個臺語連說都說不太好的同學,竟然會唱臺語歌。
「年紀這麼小就開始聽美秀,實在是後生可畏。」依佩笑說:「基隆這種草根的活力一直都存在著,如此生猛。」
-
「以前我們的美術老師,不會教導這麼多有趣的觀念,也難得有外校、跨領域的老師進入校園,與我們互動。相較之下,中正國中的美術老師很積極,也明白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訊息給學生。」
中正國中的老師們與海科館給的知識很豐富;基隆的孩子很清楚該如何去保護環境。
她稱讚道:「他們知道此時為大自然多著想一分,就能為後代保有更好的生活條件。不把沙子、貝殼帶走等,基本的教育觀念在他們這裡,是很扎實的。」
「現今網路化的社會,訊息交織得越發緊密,我們不該只侷限在某個部分,需要全面、多元的觀點,為學生們帶來相對平衡的資訊,教導他們如何在其中判斷。」
而從孩子們的角度來與他們對話,是依佩在創作時很重要的出發點與詮釋。
-
「那時一聽到公主號的音樂,大家都興奮地哦哦哦超大聲,說:『哦!我好久沒聽到了!』有些同學還會跟著旋律哼。」依佩笑說:「這些小朋友很幸福;他們的生活,原先即存有海洋的環境氛圍。」
她也感嘆,在都市長大的人們與海的關係,是直到後來透過某些知識、動機,才與它更靠近。
乘坐時光機,往返六零、七零:那個我們不曾經歷過的年代
「7、8年前,我曾半夜去過崁仔頂。看著在港口工作的人、魚市場的氛圍與環境、貨車再將漁貨運到其他市區。我很喜歡這般喧鬧、純樸的人文景觀。」
基隆港那有個法軍公墓(清法戰爭紀念園區),埋葬戰死他鄉的法國軍官。而如今臺灣人在祭祀時,是採用佛教與道教結合的方式,樂儀隊表演、供奉的祭品裡有酒。
「這個現象,讓我在印尼時,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依佩說。

印尼受荷蘭統治三百多年。
「前幾年因為熱帶雨林計畫來到了印尼蘇門答臘島北端的亞齊,那時我參觀了荷蘭公墓。亞齊戰爭後,許多荷蘭軍官葬身於此,墓園裡一座主要雕像為當時的荷蘭軍官形象,石碑造型採西方建築、上面的字大多是荷蘭文;當地人在回顧這個事件時,祭拜的過程中已融入了回教文化,在平時的穿著、語言中。」
依佩形容那時,像是乘坐了時光機,往返來回。
「在臺灣也有這般場景的存在,似乎自己與歷史事件又更靠近了些。」
-
零八年,依佩在一間以當年的臺灣來說,可以算是引進東南亞當代藝術的先驅畫廊實習,專門介紹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的藝術家。
「在當時,我們接觸到的當代藝術主流,是日本、韓國和中國。對東南亞文化的認識,只停留在新生南路那的清真寺,和少數臺北車站後站的移工們。」她說:「那時的人,找不到深入認識東南亞文化的一個出發點。」
曾有位印尼藝術家建議:「如果很想了解,那就來印尼日惹一趟吧!」

「然後我真的就去了。」依佩笑說:「當地不論是傳統文化、藝術創作,甚至是地景樣貌,都讓人有充滿活力的感受。」而那時的她,正巧在追溯父母親那個年代的生活背景。
「我發現爸爸媽媽口中的那些景象,在這裡還能找到一些線索。
這趟旅程,可以說是我與家人變得親近的原因。」
-
「我爸媽很喜歡聽鄧麗君的歌。」在印尼、新加坡和越南街上一些小店,還能聽到人們哼唱她的歌曲。「這很有趣,因為時空不同、版本不同,但在那裡國度裡,這是稀鬆平常的生活景象。」雜貨店牆上貼著劉德華的偶像照,那個氛圍帶她回到了八零年代:
「我們沒有機會經歷過的臺灣。」時代在變化,臺灣許多的老建築都被拆除;然而在東南亞,還能輕易地找到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
-
依佩父親有位從當兵時認識至今的好友,一位臺東的原住民,20多歲後去跑船,最常去印尼麻六甲海峽捕魚,大約半年才回臺灣一次。他是依佩家中少有的東南亞文化資訊之一。「原先對東南亞的認知已經存在了,直到後來真正踏上那片土地,才開始拓展自己的視野。」
「從前臺灣流行鬥雞,現在我們也找不著哪裡有這種活動;但那時在印尼爪哇島三寶瓏的老城區行走,還能看見街上有人在鬥雞。」依佩回憶道:「早期人們會使用一些自創的磨豆機磨製咖啡豆。也是在當時,我看見一個騎著腳踏車的人,座位後面載著磨豆機,現場磨豆子、沖泡咖啡給客人喝。」
她說,也許在臺南、臺東一些隱密的鄉村還能找到這般的生活模式;
可在東南亞的城市裡,仍是非常普遍的場景。
鯨魚隨著洋流環遊世界,帶我們看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
「書包對小朋友來說,是很重要的媒介,是他們跟這個環境、事件互動過程的物件。海洋書包計畫串聯臺灣、東南亞與日本等,一種知識性的傳遞,是它作為修復關係很重要的過程。」
-
「臺灣、海洋、東南亞之間的聯繫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始終在依佩的腦海裡打轉。
-
夏威夷和加州之間,有一處相當著名的大太平洋垃圾帶(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又稱太平洋垃圾島。今年六月,美國海洋環保組織《海洋航行研究所》航行至此,撈出約103噸的魚網、塑料製品與其他垃圾,是該地區目前為止,進行過最大的海洋清潔工程。
在臺灣、泰國、菲律賓與印尼都曾發生領航鯨、抹香鯨、柯氏喙鯨、弗氏海豚等擱淺事件。人員解剖後發現,原來這些海中精靈生前吞食了大量的塑料,保麗龍、漁網等,少則8公斤,多則有80幾公斤,而有次在臺灣的擱淺事件,剖出了重達84公斤的垃圾。
「鯨魚在生物鏈裡,是平衡海洋與人類的關係。而人們不斷拋棄的生活垃圾、醫療廢棄物,令牠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
-
依佩在海科館展出作品《你扔掉的寶特瓶漂流到了小島和鯨魚胃裡 》。
「鯨魚以某種姿態漂流到島上,然後人類發現牠時,這個島變成我們去認識牠的一個重要的環境、場景。但牠是吞進了許多我們人類產生的垃圾,死亡後來到這裡。」她說:「所以『這個永續』,並不是大家所期待的事,是變質的。人、鯨魚、海洋三者之間的關係,似乎是靠垃圾來連結。」
「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島民都是海洋的孩子,當擱淺事件越來越頻繁,也是海洋正在向各處呼喚緊急求救 (S.O.S),我們應該立刻起身行動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同時心中默許不會再有這樣的道別。」
嗅覺經驗:是經歷許多計畫後,慢慢掘出的寶藏
在創作最初階段,人們難免停留在視覺層面,或是心理狀態的對話形式;直到後來依佩才發現,若想讓眾人參與進一個大的概念,需要找出大家共有的經驗。
「嗅覺經驗,是經歷許多計畫後,慢慢掘出的寶藏。」她說。

一八年五月,依佩與印尼藝術家阿里安山・卡尼阿哥 (Aliansyah Caniago)在臺北植物園展出作品《無根的樹》( A Tree without Roots)。
依佩解釋,那時會選擇樟樹這個議題,是因為阿里安山的祖先,曾經是蘇門答臘島上一個王朝的國王。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樟腦是印尼出口荷蘭最重要的經濟作物,荷蘭人將樟腦製品帶回歐洲後,以高價售出。文獻記載,約在一千四百多年時,一公斤的樟腦精,差不多等於一公斤黃金的價格。那個年代,樟腦、樟樹等自然資源,比黃金價值還要高。
「但今日在衡量價值時,其實是完全相反的。我們覺得樟腦的價格應該要更低:因為它是源於自然的資源,源源不絕甚至能不斷地被複製,或者生產。」而人們對一個物件的價格與價值的判斷,正隨著時空變化。
臺灣日據時期,樟腦也是出口貿易的經濟作物之一。「我們在追溯樟腦的貿易資訊,一直都是往東北亞的貿易路線,很少去尋找東南亞的方向。東南亞本身也有樟腦的天然資源,而我們試圖去探索樟腦在臺灣與印尼之間的故事:如何將中間缺失的地方連接起來?這是《無根的樹》的創作起源。」
-
這讓我憶起年幼時,打開祖母衣櫃,迎面而來是稍稍刺鼻的樟腦氣味。
而氣味的印象是從小至今,難以抹去的。

「樟樹這個樹種,從生至死都有其利用價值。我們在苗栗找到臺灣僅存的天然工廠。他們從日據時期就已經在提煉樟腦,現場還存留了四個非常古老的鍋爐;現在已經換成新的設備了。」
工廠有一區專門囤積樟腦的廢料。將樹幹切成碎片、油水分離成樟木渣;公園遊樂設施底下的綠色墊子,是來自這些木渣的回收再製。依佩與阿里安山一步步去了解樟樹的生命過程;最後,他們買了一噸的木渣,帶回植物園現場,並將木渣拼回樟樹的型態。
「沉靜在木渣囤積場時,對樟木的氣味已麻痺;回來後才發現,即便是殘碎的木渣,也還有香氛停留。」她說:「看似已無用途的自然資源,換個角度,其實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
這件作品在臺北植物園的欖仁廣場,放置長達半年之久。
「我們一直以為它已經接近死亡。」依佩說,他們將之命名為《無根的樹》,卻在最後將它移走的過程中,發現周圍樹木因濕度充足,氣根往上走。樟木木屑中含有許多腐植質,他們也從中聞到了菌類的味道。
「欖仁廣場是植物園裡過道的交會點,居民會穿越這裡,到植物園附近的公園。」依佩回憶當時阿里安山在創作,路過的民眾會停下,和他們分享故事。有人說在和平西路那的入口,有很多樟樹,以前植物園的哪邊也有;從小就住附近的志工說樟樹的味道,讓他回想起從前很常使用樟木驅蟲,也提到它能跟哪些植物種在一起。」
-
那年植物園《無根的樹》,勾勒出許多人的記憶,也交織出依佩、阿里安山與人們的對話。
故事寄存氣味,飄盪過去、此刻與未來。

抽離自身,作為第三者來觀看
「地景藝術之父」克里斯多(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與喬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是影響依佩深遠的藝術家。
其中波伊斯的《七千棵橡樹》(7000 Eichen)計畫,是在二十世紀尾聲,極為重要的前衛公共藝術。同時也是環境保護運動積極分子的波伊斯,藉由七千次種植橡樹的過程,讓人們與所處的環境產生了連結。
-
「提醒人們應該將自身抽離,作為第三者來看觀看生活環境:『現在是不是應該要為它發聲;或是透過環境,去帶出人與環境之間的生活比重和關係。』」她說:「與環境相關的公共藝術,更多是在處理人和社會間的關係,它讓我們意識到:人在做決定時,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這些藝術家不斷地提醒我們,要與環境更平衡地相處。他們的作品,總能讓我想起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的初衷。」
-
依山生長的小孩與靠海生長的小孩,思維不同。
「跟山相處時所達到的平衡,跟海相處時達到的平衡,卻都是個循環。不論身在城市、郊區、海邊或山村,都有某種延續性的環境課題等待我們去處理。」
人在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對地渺小,該如何在這個循環裡達到平衡—這是依佩對自然與人,生命地叩問。